一曲庄严而神圣的生命赞礼——读马悦的小说《一根红丝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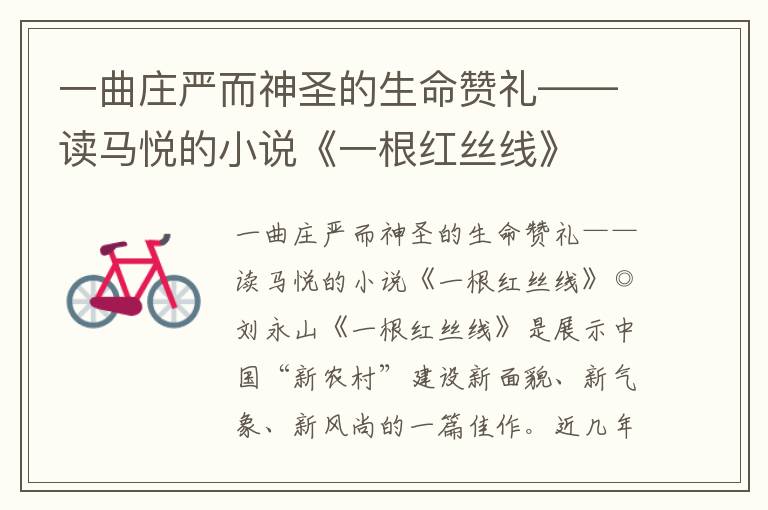
一曲庄严而神圣的生命赞礼——读马悦的小说《一根红丝线》
◎刘永山
《一根红丝线》是展示中国“新农村”建设新面貌、新气象、新风尚的一篇佳作。
近几年,民生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贫困山区移民工程、农村“新社区”建设工程,仿佛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神州大地上。那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公租房及其他改造一新的建筑,那一片片由贫困山区农民移居搬迁而建的住宅新区,那一排排规划整齐,洁净靓丽,水电路皆通,商店商场,农贸交易市场等设施齐全的新社区,以及那郁郁葱葱的绿化带、艳丽芬芳的花卉盆景、笔直平坦的柏油路和家门口突然停放的小车等诸多新生事物,无不展现出农民欢欣喜悦的心情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古谚云:若知朝中事,先问乡下人。《一根红丝线》就是中国新农村建设中绽放出的一朵绚烂的花。如果说在《牡丹花开》中描述村民刚搬到“新庄子”,内心还涌现着一种烦闷和空寂,甚至还出现了村里所有男人聚在村部大院,围堵和打骂前来视察工作的领导和村长的浮躁情绪。而这篇小说,则描写人们在“新庄子”那种恬静美好、和睦相处、为光阴日子整天忙碌不停的蒸蒸日上的生活美景。
马悦是一位注重描写农村题材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陪嫁》《牡丹花开》等,无不描绘出一幅幅十分浓郁而独具特色的乡村美景的生活风俗画,并且作品中的情感脉络是那样的炽热、细腻、深邃,表达了作者对于家乡人民由衷的眷念,对于哺育自己成长的家园那份情真意切的感激之情。在《一根红丝线》中,作者写了许多惊心动魄的生活场景,比如叙述老家拔麦子时的那种劳累和繁忙。
那时候没有收割机,有多少麦子都靠人们的一双手。尽管有护手套,半个多月的麦子拔完,手上会脱落一层皮,血泡和老茧一下子是蜕不掉的,僵硬得像个壳;小拇指受损最严重,不但被麦秸秆打出血泡,指甲盖也瘀血了。麦子拔完,等那饱满瘀血的指甲慢慢蜕去长出新的来。
刚刚开始拔麦子,一两天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不说苦的,浑身酸痛,双手起泡,被麦虫叮咬得浑身起皮,晚上像蚂蚁在周身奔跑。手火辣辣地烧痛,那些血泡非得用火针烫了才能结痂,不然手搭不到麦秸秆上。疲劳无处不在,来不及烫血泡,两只眼睛就跟抹了胶水一样,一切都被黑暗吞没。
谁不想起个大早赶在别人的前头呢?在蹲下身子的那一刻才知道浑身有多僵硬,像吃了椽子,腰都弯不下来。手的骨节生疼,蜷缩不来。咬着牙蹲下去,一只手伸向麦秸秆。拔下第一把时,几乎用上了浑身的力气,再拔下一把,一把又一把;另一只手伸向麦秸秆,吃力地拔一把,那长在地上的麦子,它的根系就好像扎在一丈深的地下,脸上的肌肉都疼得扭曲了。
小说最终的意象是以写人的精神面貌和人内心的喜怒哀乐、离合悲欢为主轴线的。这篇小说,是围绕着赵学青老汉与乔惯一家人的恩恩怨怨而展开的联想。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情节也很简单。但作者如一名精心培育花卉的园丁,在有限的土壤里展开了无限的联想。运用深沉、精致、传神的笔墨,如数家珍一般,娓娓道出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感人至深的细节。
赵学青是一个身份低下的羊把式,“个头矮小,人瘦,又是罗圈腿”,与“高大魁梧,穿着讲究,又是村会计的乔惯相比较,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当赵学青为了挽救一个羊羔子的生命,抱着羔子跑向家,想让女人把羔子焐进被窝里,竟然看到自家“炕上的被窝里睡着乔惯”。刹那间,“以前的一切美好,在羊妈妈的悲切地呼唤声里变成了一摊狗屎。”朋友妻,不可欺。任何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会容忍这种耻辱。于是,在“那个有风的夜晚,他手里拿着一把刀子,一脚踏开了乔大炮的家门”,还没等到乔惯和他老婆反应过来,乔惯的脸上已经挨了一刀。从此,“乔惯的左脸上留下一个刀疤”。从此,“他对女人的心也死了。”
生活中,做一个女人是很难的。她们心里往往承受着比男人多数倍的痛苦,尤其是那种伤风败俗的丑事,受伤害最大的也是女人,会压得女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女人是如何被乔惯所欺辱,她内心的伤痛究竟有多深,小说并未详细注解,也许作者不屑于解说。然而,女人却像一个奴隶一样,默默地用行动去赎自己的罪过,即使身患绝症,也是强忍着,直到“女人晕倒在炕上”。
当女人从医院回来,已经预感到自己病情的严重,“她的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神情异常安宁”。也许女人早已明白,唯有她的生命,才能换回男人对她的谅解。死,对于她而言,只是一种解脱罢了。因此,在口唤的头天晚上,女人说想换个大水,却并不让两个女儿侍候,而是让男人把一桶热水提到里屋,这分明是女人想用那种方式给彼此一次和解的机会。这种蒙太奇式的电影画面,这种浸入骨子里的感人肺腑的生活场景,是对生命庄严而神圣的洗礼。这个即将结束生命、超脱生死、走向天堂的女人,心中无比悔恨和悲伤,想把所有的爱恋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与自己陪伴一生的男人,他们之间没有一句对白,但浸透在纸页上的浓浓情愫却胜过千言万语,让人读着心痛,让人读着落泪。
在清洗的过程中,女人精神出奇的好,也很平静。他拿着汤瓶,站在凳子上替她倒水。女人站在一个盆子里,浮肿的肌肤泛着青白,肚子稍微消了些,腿还肿胀着。女人已经不在乎身体的负重,她需要完成一项神圣的洗礼。
水哗哗地流淌着,他的眼泪也流淌着……
人生就是这样怪异,失去的才是生活中最美好的。当女人离开两年后,时间像个筛子,把女人的缺点过滤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好。那些好,就像闪亮的贝壳堆积在他的心岸上。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一束月光幽静地铺洒在炕的一角。那束光亮似乎从天庭里扑下来,有种虚幻的感觉,好像在召唤他沿着这道光亮到天堂那边去。
人生若梦,时光如流水。当我们大梦初醒,睁开惺忪的睡眼,岁月的篇章已经轻轻地翻过一页,生命的航船已经起锚,驶向另一个港湾。往昔的痛苦、愤恨和悲伤,已经被呼啸的海风抛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而那冉冉升起的朝阳和唧唧吟唱的海燕也在昭告着人们:新的一天开始了!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随着女人的口唤,乔惯也得了脑出血死了,又搬进“新庄子”,似乎赵学青与乔惯之间的恩怨情仇也渐渐地消散了。可是老天爷似乎有意捉弄人,让早起的赵学青老汉走在村巷子里,竟然巧遇了乔惯的老婆和他的儿子以及襁褓中啼哭的婴儿。乔六六竟然还说“生下的娃子要能认个回族干爹就好了,这一辈子都无病无灾。”当乔六六急切地想把老妈怀里的孩子递过去,赵学青却扭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这种巧遇再一次激起赵学青对乔惯一家人的愤恨,“他有些气喘,也有些愤怒,胸脯起伏着”。对于乔惯所造下的孽,赵老汉心里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起码让他知道了那个小孽种身体不舒服,他会不会像他爷爷那样突然死去”。
“老叔,救救我孩子,你就答应了吧……”这种无望的乞求,一个小生命嘤嘤的啼哭,仿佛“不是从屋外传来的,而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很微弱,却像长有无数只手撕扯着他,让他浑身冒汗,烦躁难耐”。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是如此的珍贵和亲切。即使动物,那只失去了孩子的羊妈妈,亦是难舍母子分离的悲痛。这又让赵学青老汉怀念起自己的女人,以及女人刚刚生下三天就夭折的那个孩子。当儿媳妇十分怜惜地告诉赵学青老汉羊羔子已经死了,“倏地,他的心似乎被谁紧紧地捏着,有一桶水从头顶浇灌下来,他感到浑身冰凉。”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结束了,羊妈妈悲痛的神情深深地触动了赵老汉内心深处的良知,再一次唤起了他心底里的善良和仁慈,激起了他对生命的无限敬仰和感激之情,同时又使他联想到另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在结尾处,作者的情感脉络依然表达得十分细腻,那种庄严肃穆、意境深远的细节,不仅使小说主题达到高潮,更使人物的人性之美得到升华。
他知道那个村庄有多远,他一刻都不敢停下来。走了大约五里地,没有碰上一个人。这时候东方放出一丝亮来,天空的云以静谧的姿态迎接早霞的到来。四野渐次明晰,身后的村庄传来牲畜的叫声,远处阵阵机器的轰鸣。葡萄园在晨曦里块块相连,繁密的叶片在露珠的滋润下释放出淡绿色的雾霭来,如梦如幻。他没有时间驻足观望,硬化的道路助长了他步行的速度,他好像真的要去赶一场葬礼。
这是个漂亮的婴孩,眼角很长,眼角稍稍往上翘着,有一对浅浅的酒窝。大概太过陌生,婴孩努力睁大眼睛辨认着。孩子想笑,无奈他还没有学会笑,于是攥紧的小拳头动了动,紧接着两条小腿使劲地蹬了两下,然后哭了。多么鲜活的小生命!赵学青感激地望着,并对着小脸默默地念着,一边对着婴儿吹了吹,然后抬起头来说:好了,从此以后,这个孩子会无病无灾。
当赵老汉接过乔六六老妈递过的一根红丝线,拴在婴儿的手腕时,像在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神情是那样的虔诚、庄重而心无杂尘。一切恩恩怨怨皆在生命的感念中消弭,一切烦恼和羞耻皆在这种庄严而神圣的仪式中得到释然。
发掘人性之美,体现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是此篇小说中所表达的深刻内涵,也是这篇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在描写一般共性的基础上,又凸显出特殊意义的闪光点。
刘永山,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吴忠市作协会员,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