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冬林·一棵野桃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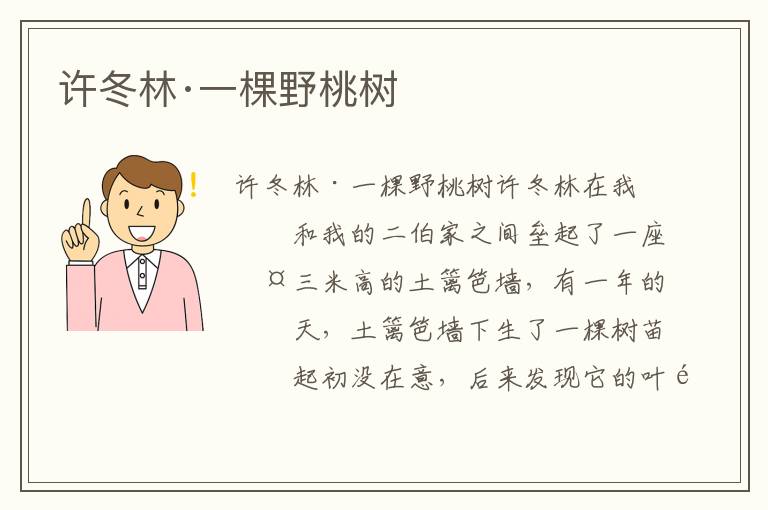
许冬林·一棵野桃树
许冬林
在我家和我的二伯家之间垒起了一座两三米高的土篱笆墙,有一年的春天,土篱笆墙下生了一棵树苗,起初没在意,后来发现它的叶酷似桃叶,便也时常关注起它来。我猜想,这棵桃树可能是我无心种下的。我喜欢到处捡一些桃核杏核回来玩,玩过之后便随处丢撒。也许,这棵桃树就是在我随意丢撒间有了一次幸运。它幸运地在瓦砾间抓到了一捧泥土,幸运地在两堵墙之间抓住了几尺阳光,然后是空气和湿度,接着萌芽,破土而出,有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超然。
我想,我也是幸运的,在时光的河流上,属于我的生命流程充其量不过七八十年,一棵桃树的流程也不过十来年,而在这其间,我的生命和它的生命竟有一小截叠合,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幸运。
小桃树便在我的珍视和盼望里渐渐长高长大,五年之后的一个春天,它打了些红红小小的花苞,可是开得却很迟。当别的桃树谢尽了芳菲时,它才三三两两地次第开放,花朵很红,红艳艳的一片,红得热烈、张扬、活泼,似乎想淋漓尽致地宣泄它开放的热情和美丽,那土篱笆墙因此而多了几分热闹。奶奶来看了,然后冷冷地丢下了一句:是棵野桃树!原来野桃树的花开得红而迟,奶奶说它成不了气候,结不了什么好果子。可是,我还是不愿相信奶奶的话,因为一直以来,她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她总爱在父母面前唠叨,说一个丫头还读什么书,将来好了别人家,真是浪费,以至于我后来十几年的读书生涯一直怀着负罪的心理。
那棵野桃树因为在土篱笆下,没有多占一份泥土,也没有多占一份阳光,因而获得了继续生存下来的权利。那花儿确实开得好看,每片花瓣都染上一片红晕,显得更加生动、健康,我觉得那片富有活力的绯红似乎更能承载一份秋天的希望。三月过了,花儿落了,红红的花瓣随风飘扬,有的落在瓦砾上,归入泥土;有的落在屋顶的砖瓦上,高高地干枯在四月的阳光里;有的飘到小河上,随流水而去,瘦弱的树枝显得颇为忧伤和冷清。美丽总是就那么一刹那,总是太短太短,就像乡下的新娘——童年的乡下最热闹的事就是看新娘,我那时以为女人做了新娘就永远是新娘,就会永远那么干净而美丽,天天坐在房间里,只是偶尔出来羞涩地笑笑,那只是对着我们这些孩子。可是只是三天,这些新娘便扛锄拿锹地下了地,一年后便是手里捧着饭碗怀里搂着孩子,门口晾了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尿布,走起路来快了,说起话来嗓门大了,脸色黄了,皮肤皱了。乡下的姑娘就像桃花,出嫁的那天开得最美最艳,然后一夜风雨,便凋谢了。
当别的桃儿已经长得肚大腰圆,满脸涨红时,野桃树的桃儿还是那么小小的、青青的,躲在枝叶丛里,它的生长似乎比别的果实总要慢一拍子。中秋过后,田里的稻子已收割回仓,家里的人闲闲地坐在门口,我看见野桃树上的桃儿都已经泛起了红晕,很多已经长得开裂。我摘了一个轻轻一掰,开了,里面是鲜红的瓤,原来野桃是从里往外红的,它成熟得那么谨慎而谦虚。我尝了尝,绵绵的、软软的、香香的、甜甜的,我又摘了几个捧到奶奶面前,奶奶尝了尝,咂了咂嘴说,苦中还有点甜柔,就是太小了点。可是我已经很高兴了,我的野桃树它终于捧出了自己的果实!
现在,奶奶早已去世,我的父母已经老了,他们喜欢常常站在门口,看我回去。在乡下,他们常常引我为自豪,引我为欣慰。他们觉得,在书声朗朗的校园,在抑扬顿挫的讲课声里,有他们女儿的一个声音;在报刊的大大小小的豆腐块里,偶尔有他们的女儿的一个名字;在读书不多的祖祖辈辈里,有我这么一个子孙,用墨香巧扮自己。
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那棵野桃树啊,艰难地抓住了一捧土壤,固执地想结些果子。我不愿我的生命里只有三月,只有那短暂的绚烂。而我那些儿时女伴,她们也都和我一样,早已出嫁。她们依然如从前的新娘,走路快了,嗓门大了,脸色黄了。我不知道,当她们在门前门后种桃插柳时,是否想起,这样的风景已是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了。我愿她们的女儿做一棵真正的桃树,能够理直气壮地站在土地上,站在阳光里,她们有三月的美丽,更有八月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