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孟东野序原文,注释,译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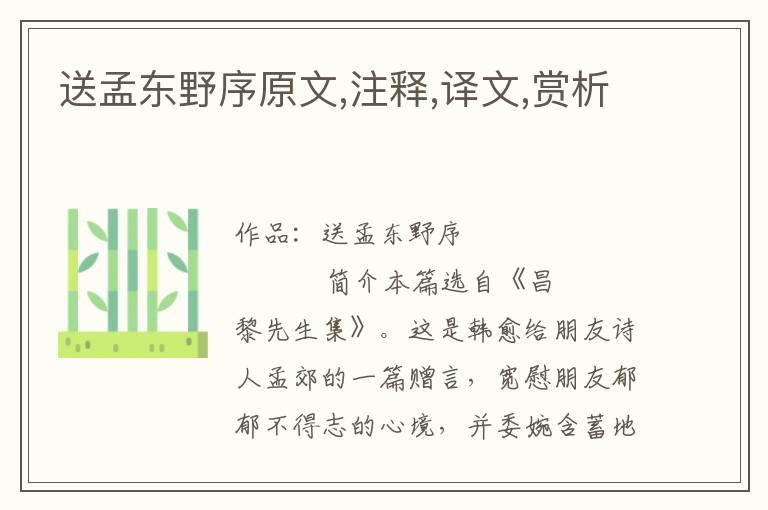
作品:送孟东野序
简介
本篇选自《昌黎先生集》。这是韩愈给朋友诗人孟郊的一篇赠言,宽慰朋友郁郁不得志的心境,并委婉含蓄地批判了压抑人才的统治者。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①、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②。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者奚以喜,其在下者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注释
①咎陶(ɡāo yáo):传说中的人名。 ②木铎(duó):木舌的铃,古代用于施政、传令、召集和晓谕百姓。
译文
大凡事物得不到平衡就会发出鸣响。草木没有声音,风扰动它便发出声音;水没有声音,风使它激荡而发出声音。水波飞溅,是因为有东西来阻遏它;水流湍急,是因为有东西来梗塞它;水面沸腾,是因为用火来烧煮它。金属、石头没有声音,如果有人击打它便会发出声音。人们发表言论也是这样,心中有所不平而后见之于言辞,他的歌唱是有所相思,他的哭泣是有所怀念,凡是从口中发出而成为声音的,岂不都是有所不平的吗!音乐,是郁积在心中而发泄于外形成的声音,它选择那乐声优美的物体借以表现:钟镈、磬、琴瑟、箫管、笙、埙、鼓、柷敔等八种乐器,便是物体中易于发出优美乐声的器具。那苍天对于时令的更替也是这样,它选择能表现季节特点的事物借以发声。因此借鸟儿啼叫来表现明媚的春日,以迅猛的雷声来显示炎炎盛夏,以唧唧秋虫来标志萧索的清秋,以凛冽朔风来体现严寒的隆冬,四季的互相推移轮转,难道不是必定有所不平吗?
这对于人类也是同样的。人类声音的精华是言语,文辞对于言语来说,又是它的精华了,更要选择善于文辞的人来借以表现。在唐尧、虞舜时代,咎陶、大禹都是善于文辞的人,便以他们来做时代的喉舌。夔不能用文辞来表达思想,就又自己凭借创制的乐曲“韶”来抒发感情。夏朝的时候,太康的五个兄弟作歌来讽刺他。伊尹作文表达了殷商的兴盛,周公的著述体现了西周的昌明。凡是记载在《诗经》、《尚书》等六经中的著述,都是文辞中最好的。周朝衰败的时候,孔子及其弟子各有言论立说,那声音宏大而久远。《论语》中说:上天要以先生(孔子)为宣谕教化的木铎。这难道不可信吗!周朝末年,庄周用他的夸饰荒诞的文辞来表现自己的时代。楚国是个大国,它灭亡之时,借屈原来表现国破家亡的痛苦。臧孙辰、孟轲、荀卿,是借道义来发表见解的。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辈,都以他们的言论、学说各抒己见。秦朝兴盛,李斯以文辞来表现它。汉朝时,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这一时期最擅长文辞的作家了。秦、汉之后的魏、晋,文辞虽然达不到古代的水平,然而也从未断绝。就其中好的来看,它们的声韵是清淡而轻浮的,它们的节奏是繁杂而急促的,它们的文辞是华丽而哀切的,它们的思想是懈怠而放肆的。那些文章言论,杂乱而没有章法。可能是老天厌恶魏、晋的德行而不去管它们吧?为什么不让那些真正擅长文辞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唐朝统治天下之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以自己的才能而咏唱撰述。现在生存于世上而身居下位的孟郊开始以他的诗鸣响于世,他的诗超过魏、晋,不懈怠便可追及古人,其他则逐渐地接近汉代的人了。跟我交游的,李翱、张籍是其中最突出的。这三位的辞章文采确实善美,不知道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平和以便让他们来歌颂国家的昌盛呢?还是要使他们的身体遭到困穷饥饿的折磨,使他们的心肠蒙受忧虑愁苦的煎熬,让他们吟咏自己的不幸呢?这三个人的命运,都取决于天意啊。那么,他们身居高位,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屈居下层,又有什么可以悲哀的?孟郊到江南去任职,好像心中有抑郁难平的悲慨,因此我便用他的命运取决于天意这番话来宽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