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宝光《岛》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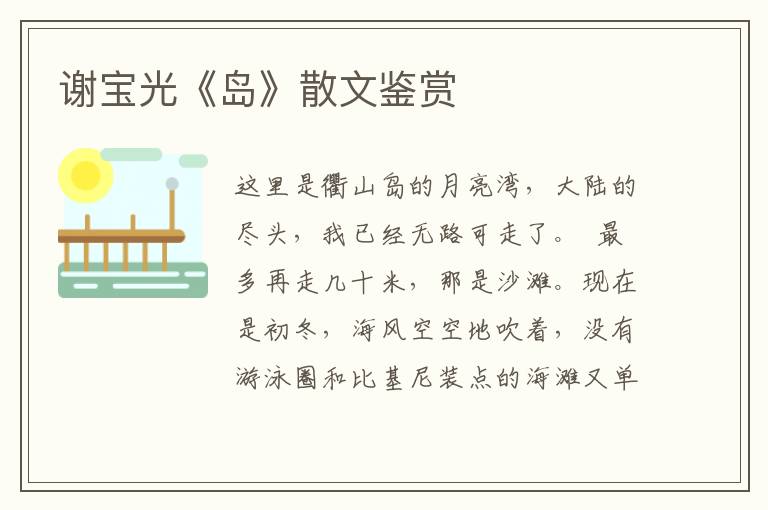
这里是衢山岛的月亮湾,大陆的尽头,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最多再走几十米,那是沙滩。现在是初冬,海风空空地吹着,没有游泳圈和比基尼装点的海滩又单调又荒凉,废墟一般。在一片废墟中,散布着许多斑斑点点的小石头,如果俯下身来看,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不是“斑斑点点”,而是“聚石成林”。我用蚂蚁的视角拍一颗石头的时候,大海如同一块辽阔的玻璃面倾倒过来。风很大,海浪一边咆哮,一边咀嚼这些石头,留下一层层消化不良的泡沫。
我在那里走来走去,一些人和我一样茫然走来走去,其实这里和那里,仅仅字面的差别。因为无论站在哪个位置,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远处斑点似的渔船,除了单薄的灰绿便一无所有的岛屿,灰茫茫向着天地交界处奔涌的云和水……
这一刻望着大海的人们,不是哲学家,起码也是诗人。他们神色空洞,头发劲草般在空中扬起。
失语是难免的,没有形容词可以拯救你眼里的一片苍茫。
干愣愣地和大海对视是很尴尬的,总得做点什么,那就捡几块石头吧。满地都是石头,除了细沙,沙滩上剩下的就是这些形状各异、长相粗糙的碎石,海浪也没能洗刷干净它们身上疲惫的肤色。我的脸差不多也这样,被初冬的海风洗得发白。已经走到地的尽头,我又开始遥望海的边界,可哪有什么边界啊,只有海浪的褶皱起伏不休。还是捡石头最实际,近在眼前,弯下腰就可以触摸,捡起一颗,一颗的命运便就此改变。它们在此浪迹了多少年啊。
听到有人在剖析石头的质地,说:“这块好啊,你看这一圈圈均匀有致的纹路,多像石头的年谱。”
我没有那么多的讲究,随手捡了三颗。其中两颗其貌不扬。另一颗有点怪,通体黄褐色,半个手掌大,上面密布着很多细孔,肤色粗糙,样子像一个心形。我有点得意,拿给边上一个茶室的工作人员看,那人一下子就揭穿了这颗石头的骗局,说,这是个砖块。砖块?难怪看上去不伦不类。我好奇是谁把它打磨成这样的,它又经历了多少次的挪动,才最终在这片沙滩上安家的。
现在看来,命运的被动迁徙又将在它身上开启了。
一块石头只要保持足够深的沉默,它就是自由的。不管在哪。
此时,有块硕大的乌云悬在海岛上空,但并没有雨,雨即将落下但是还没有。乌云加快了时间的流动,下午和黄昏在一群人头顶秘密集会,几乎瞬间完成了词义的交接。只有很远的海面上有光,金丝一般好看的光,从乌云四周的边界流泻而下。
只有我们在阴影中。
离开海滩,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贴着海岸线飞驰,接近一座海湾渔村的时候,车窗外的一个小岛忽然被照亮了。那个岛之前看到过,但并未在意,岛太多了,岛与岛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岛其实都是同一个。那些无人居住的島没有名字,或者有而我们不知道,就算知道也分不清谁是谁。此刻,我们所在的衢山岛周围,盘桓着很多这样寂寥的小岛,蘑菇头一样从海面冷不防窜出来,高高低低的植被在上面相互倾轧、叠乱,散发出一种无精打采的黛绿;岛的底部裸露着黄褐色的岩石,在岩石与植被之间有一道天然的分割线,两种颜色呈现极致的反差,但互不侵犯。所有的岛都是这样。
现在,那些岛中,有一座,因为那块乌云的飘走、光的忽然照亮,而被一车人看见了。不,不仅是看见,看见多么庸常,是蓦地发现,那袈裟一样被佛洗礼过的光泽,将岛从一片汪洋中湿漉漉地举了起来。那不是岛,而是海上的宫殿。众人忍不住惊呼。仿佛之前它并不存在,仿佛它在惊涛中隐忍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刻的现身。哪怕只有车上十几双眼睛在注视,哪怕没有观众,它浴光重生,那光是金铜色的,透着微微的寒意,醒目而又孤绝。
在几乎一闪而过的凝视中,我相信那座岛抵达了永恒。
入住凉峙村的一家民宿,我的房间窗户正对着海。
从岛上醒来。浓浓的海腥味顺着凉峙村的窄巷鱼贯而入。我喜欢这种味道,真实,像海打出的饱嗝。
上午九点,乘坐一只锈迹斑斑的渔船出海,摇摇晃晃中,望着视线里渐渐萎缩的岛屿,竟生出一丝出征的悲壮感。这种感觉先前是没有的。前天来时,坐的是宽敞的客轮,在密闭的船舱内,人被包裹着,海浪的凶狠隔绝在外,身体陷在绵软的座椅里昏昏欲睡,唯有客轮马达的震颤自臀部阵阵袭来。
现在的感觉,有点像被抛到海上,与海的皮肤真正贴在了一起,是一种斩断了后路的漂流。你看,浪一起,身下的渔船就会抖三抖。脚下,不足五平米的甲板,几个人裹着厚厚的救生衣,挨着舷杆,挤在两条窄窄的铁凳上,稍不留神就要滑落海里。渔船简陋,头顶虚设的遮雨棚,是由几根黑乎乎的竹篾搭的,却没有布。就这样裸露在蓝天下。没人说话,大家歪着头,出神地望着大海,那贫瘠的荒原,仿佛有魔法般的能量,在他们瞳孔间抹上了一道神秘之光。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十分钟,而我们沉默的理由却是如此形而下:头顶那根锈得掉渣的烟囱实在是太吵了,像一只性情烦躁的野兽,无时无刻不在嘶吼着,“突突突”“突突突”,有节奏地冲击着我们的耳膜。听不见旁边的人在说什么,只见嘴巴努力地一张一合,几个勉强冲出了马达包围圈的词,到达耳边的时候,也形同呓语。在浩渺的海上,我们被取消了听觉,成了一群聋哑人。我们以聋哑人的姿态看海,我们不说,只看。
一种声音一旦成了常态,也就在我们的意识里隐形了。事实上,耳膜的种种不适,因为那根烟囱的持续冲击,反倒习焉不察了。上午的阳光正好,铂金般洒在脸上,温度不冷不热,风也不紧不慢,一切都刚刚好。看着周围那些忽近忽远的小岛,想起了科塔萨尔的小说《正午的海岛》。让人着迷的叙述。每读一遍,眼前便浮现一座乱石丛生的荒岛。眼前那些岛也是荒的,杂树,乱石,适合幻想家幽居。我们这是要去哪呢?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有问。就这么一直漂着。也许要去的就是科塔萨尔描述过的那个希腊小岛,让我迷恋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是的,不知道要去哪,去哪都无所谓,只要是大海、渔船和无人海岛,让幻想再自由地漂一会。
漂了一个多小时,船突然停了,黑烟囱也停止了咆哮式的排放。从甲板往船尾俯瞰,冒出两个头,其中一个光秃秃的。从年纪和形态上看,应该是两父子。他们开始撒网,一张油绿的巨网被抛了出去,网连着船尾两侧快速转动的轮轴,很快沉到了深海。会有多少倒霉的鱼不幸落入网中?漫无目的漂流,到了这里,总算出现了一丝盼头。我站在甲板上看网消失的那片水面,除了两道铁船压过的折痕,什么也看不到。那些看不见的鱼此刻或许正与密网做着殊死搏斗呢。
事实很快击溃了我的想象。半个小时后准备收网时,我兴冲冲跑到船尾,盯着网一寸寸往上拉,几十米长的绿油油的大网,在接近最后半米的时候,才出现了一点白。零星几条鱼虾,一个脸盆都装不满。品种倒是丰富,鲶鱼、沙鳗、黄鱼、带鱼、螃蟹,还有一种叫“沙秃”的鱼,体型都很瘦小,一个个翻着白皙鲜亮的肚皮。
从岱山作家复达口中得知,因常年捕捞,舟山近海几乎没多少鱼了,当地渔民一般都驾船二十多小时到与韩国交界的海域捕捞,常常去一趟就是十天半月,甚至更长。这句话搅动了我身体里的某个部分,和鱼无关,而是这样的状态——十天半月地漂在海上。漂着。摇晃、动荡、船噪,以及无休止的时间、不可測的天气……这需要一颗多么强大的心脏?当夜晚降临,面对不断繁殖的漆黑与空洞,那些渔民依靠什么来抵御虚无的侵袭?或许这多少有些文人式的多虑。我更愿意进一步理解,多年的捕捞生涯,他们早已把大海修炼成了生活的广袤大地;而大陆,永远为浪尖上舞蹈的他们擎着一盏不灭的灯火。
那个年长的渔夫六十多岁了吧,套一件水蓝的塑料防水裤,等待收网的那段时间,他一直愣愣地站在船首那个转轴边,间或点起一支烟,和温煦的海风一起抽着。烟抽完了,还有大把闲置的时间,他扶着舷边一根铁柱,双目低垂,张望着海水,似乎在默想着什么,又像在和自己专注地对话。这样的姿态是迷人的。透过驾驶舱的门框,我把这一瞬间永恒地截取了下来。
收网之后,渔船调转了航向。我以为漂流就这样舒坦地结束了,却忽然一股刺鼻的柴油味腾起,直呛肺腑,胃里有种翻江倒海的征兆,两腿松软,头也开始晕眩。我晃晃悠悠走到船的中部,摸到一块铁皮板躺了下来,目光勾住天上的一朵云,感觉身体正和自己一点点剥离。我告诫自己挺住,千万不能吐,说不出缘由,似乎非要和大海较一较劲,结果憋得脸红气胀。半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衢山岛。啊,结实的水泥地,双腿一下就立住了,全身回血般,瞬间和失去的自己重逢了。这时,我听见一位女诗人轻声嘀咕了一句:“他(她)自海上归来,脸上带着泡沫的眩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