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太湖石记》原文,注释,译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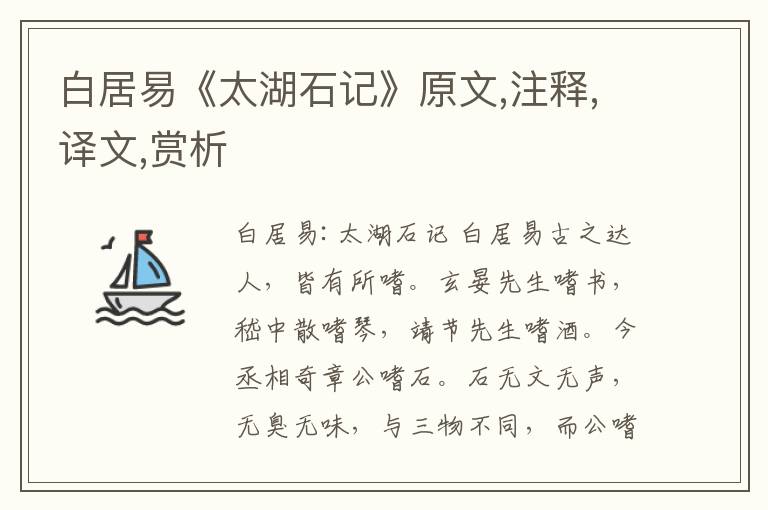
白居易:太湖石记
白居易
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书,嵇中散嗜琴,靖节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众皆怪之。走独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约有云;苟适吾志,其用则多。诚哉是言!适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
公以司徒保釐河洛,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精葺宫宇,慎择宾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
先是,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丘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稜锐刿,如剑戟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跧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者。风烈雨晦之夕,洞穴开歕,若欱云喷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霁景丽之旦,岩崿霮,若拂岚扑黛,霭霭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旦之交,名状不可。撮要而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其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常与公迫视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以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将尤物有所归耶?孰不为而来耶?必有以也。
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千百载后,散在天壤之内,转徙隐见,谁复知之?欲使将来与我同好者,睹斯石,览斯文,知公嗜石之自。
会昌三年五月丁丑,记。
太湖石,盛产于太湖流域。石在湖底浪激波涤,久历年所,孔穴自生。它们的审美价值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为文人雅士所认识。至迟在南朝就有人开始用以点缀庭院。誉之为“司空石”,意谓它是石族之最,其地位与宫阶中一品司空相埒。文中说:“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并非过誉。
文中说的“丞相奇章公”,指的是牛僧孺。牛僧孺,字思黯,历相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封奇章郡公。他是中唐牛、李党争的党魁。与李德裕交恶,长达三、四十年之久。 白居易在政治上始终倾向牛党。晚年定居洛阳,彼此过从尤密,时有唱和。从他们酬唱之什中得知,牛僧孺这些太湖石主要是由其僚吏、开成初任苏州刺史的李道枢提供的。牛僧孺在诗里提到“为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鲸;利涉余千里,山河仅百程”,与文中所谓“钩深致远,献瑰纳奇”正合。
会昌二年(842)初,牛僧孺由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调东都(洛阳)留守,即所谓“保釐河洛”。其时,牛已失势,乃於洛阳城郭营建东第南墅,以为晚年游息之所。本文称牛为“达人”,说他“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慎择宾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这些都是曲为讳饰的说法。
“厥状非一”以下一大段文字,是本文最精采的部分。作者象是高明的导游,一经他着意描绘、渲染,原本无生命的静物——列置于东第南墅中的太湖石,顿时神采飞动,富有生机,它们都能给人美的感受。有的像高耸入云微露峥嵘的怪石(“盘拗秀出·如灵丘鲜云者”);有的矜持端庄地挺立着,活像是个道家仙官(“端俨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的纹理细密,与美玉雕就的带柄酒勺相仿佛(“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的稜角锋利如同剑戟一般(“廉稜锐利,如剑戟者”);有的像蜷伏的巨龙正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或像行将展翅翱翔的凤凰(“如虬如凤,若跧若动,将翔将踊”);有的像格斗的厉鬼或追捕猎物的走兽(“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一到急风暴雨的夜晚,洞穴仿佛是庞然大物张口狂笑,吞云喷雷,令人望而生畏(“风烈雨晦之夕,洞穴开歕,若欱云喷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待到雨过天晴,阳光明媚的清晨则别是一番光景,坎穴幽深,薄雾缭绕,又变得那么和霭可亲(“烟霁景丽之旦,岩崿霮,若拂岚扑黛,霭霭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晦明变化,难以名状。总而言之,“三山五岳,百洞千壑”,仿佛全都浓缩凝聚在此。置身其间,因小见大,尺幅千里,尽收眼底。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东第南墅怎不令人感到称心惬意!欣赏这段文字,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作为旅游者观赏园林胜景,必须“迫视熟察”,下马看花。在细致观察的同时还得驰骋想像,看得景观的精神所在,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臻于融合,从而获得美的享受。此其一。其二,写作山水旅游文学,要善于运用巧比妙喻和化静为动的手法。这样才能把景物写得活动跳脱,逗人联想,进而引起人们神游以至身历其境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