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龙《刈麦》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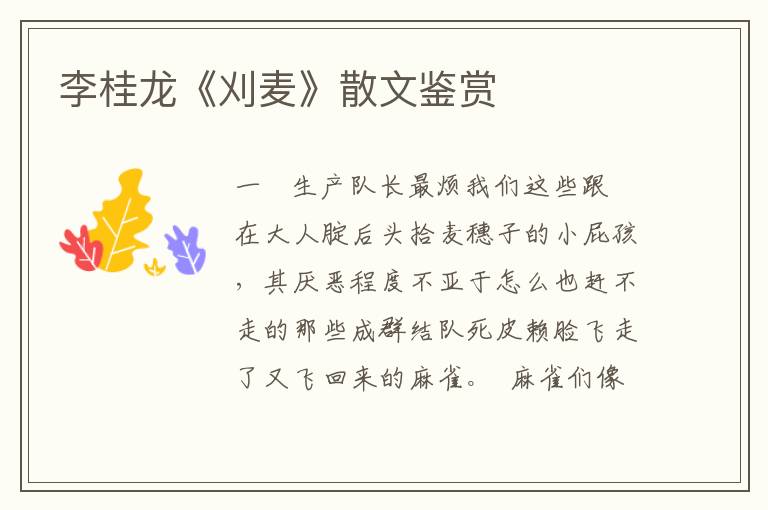
一
生产队长最烦我们这些跟在大人腚后头拾麦穗子的小屁孩,其厌恶程度不亚于怎么也赶不走的那些成群结队死皮赖脸飞走了又飞回来的麻雀。
麻雀们像一阵小旋风,“呼啦”一声落在麦地里,一只只贼头贼脑,一边飞快地啄食着落在地里的麦穗子,一边警惕地环视着割麦子的大人和我们。二能从怀里掏出弹弓和石子。弹弓架是用柳树杈子做的,拉皮用的是自行車轮胎气门芯,弹兜是问修鞋匠要的修鞋的牛皮。古诗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记述,意即砍竹做弓以泥丸射鸟兽。后来发展成一种武术器械。二能闭起一只眼,扭着嘴,囊着鼻子,瞄准那群啄食麦穗子的麻雀中的不知哪一只,拉长,松手,“嗖”一声,麻雀们惊慌失措地“呼啦”一声飞走了,接着小旋风一般又落在了不远处,继续觅食。我们跟着二能跑过去,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一只受伤的麻雀,连一根麻雀毛也没见。
我们不但不出活,还碍手碍脚,净帮倒忙。大人最担心的是小孩跟在镰刀后头,镰刀可是不长眼的,要是碰到镰刀上,无论划在哪里,都比害眼还厉害。一会儿,这个被麦茬扎破了脚,一会儿,那个被癞蛤蟆吓得哇哇哭。生产队长极不耐烦地皱着眉,挥挥手,去去去,上一边看蚂蚁爬树去!早安排一妇女用筢子把落在地里的麦穗子搂得一干二净。
看着生产队长气势汹汹的样子,我们乖乖地来到地头槐树下,一个个无精打采。就二能像是耳朵里塞了驴毛,仍然一个人跟在割麦子的大人腚后头。二能确如其名,好充能。生产队长把镰刀往后腰里一别,揪着二能的耳朵,把他提溜到槐树下。二能冲着生产队长呲牙咧嘴,挤眉弄眼,一股子不服。生产队长刚走,二能揉揉通红的耳朵,嘀咕了一声,胡汉三!
胡汉三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大恶霸,专门欺负穷人,最后叫潘冬子给烧死了。因为在这之前,胡汉三烧死了潘冬子的妈妈。在熊熊的火光里,潘冬子的妈妈牺牲前,深情地充满胜利信心地唱道:“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我们都会说胡汉三的那句台词:乡亲们,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你们谁分了我的房子、分了我的地,都给我拿回来;谁吃了我的粮食,都给我吐出来!
我们一群十多岁的小学生被学校安排星期天支援生产队的麦收大忙,却被生产队长撵得屁滚尿流,乖乖地来到地头槐树下无所事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一会儿,就都有自己的活儿干了。毛眼用臭球在地上画个圆圈,把慌慌张张的小蚂蚁圈在里边,蚂蚁们正忙忙碌碌地往巢穴里储存食物,一时间被熏得晕头转向,在臭球画的圆圈内急得团团转,就是出不去。小巴狗从挎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迎着太阳,把聚光点对准“突围”的蚂蚁,一会儿,那只蚂蚁就冒出了一股青烟。二能揉着通红的耳朵,满地里追逐气喘吁吁的青蛙。有一只被俘的青蛙的肚子被二能用麦秸吹得溜圆,一边吹一边说,我叫你拧我耳朵!把青蛙放在地上让它跑,它却跑不动了。二能终于把气撒出来了,但撒气的对象不是生产队长,而是可怜的益虫青蛙。自然从家里装了一盒洋火,堆一堆焦干的麦秸点着,揪一把泛青的麦穗子放在火上燎,两手搓几下,撅着嘴,轻轻地把搓掉的麦皮吹掉,手里剩下的就是燎熟了的麦粒籽。看看一双双贪婪的眼睛,自然迅速地把麦粒籽揞进嘴里,呱嗒着嘴使劲地嚼。就有几个流口水的在一边干看。黄毛丫突然捂着嘴吃吃地笑,大家瞅她,她指指得意洋洋的自然,大家又一起把目光转向自然,大吹迅速地喊道:黑嘴鼬子!
自然搓燎熟了的麦穗子把两手搓得黢黑,往嘴里揞麦粒籽的时候,手又把嘴弄黑了,嘴唇四周像长了一圈黑胡子,活像黑嘴鼬子。
二
第一次正式下湖割麦子是1981年。那一年,我高中提前毕业,果断地结束了对学业的追求,怀着“回到农村体验生活,像柳青一样写一部创业史”的雄心壮志回到了家里,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回到家里,正赶上生产队割麦子。第一次被生产队长当做一个整劳力安排割麦子,心里充满了被认可的激动和喜悦。生产队保管员邱二大爷识几个字,作诗一首给大家鼓劲:“风在麦地乱打滚,云在天上怪悠闲。小麦煎饼就咸鱼,你说解馋不解馋。”
出工的男女老少各自带着磨得锃亮的镰刀,围坐在地头靠近铸造厂墙根下的荫凉里,说长道短。不管男女老少,到了湖里就放松了,没有不说的笑话。谁家的闺女肚子大了,娘气哼哼地问,跟娘说实话,谁的?闺女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自然的。娘抄起笤帚就往闺女腚上砸,自然的?你怎不说是天生的!闺女捂着脸哭道,不是天生的,娘,就是自然的……后来才知道,那个男的叫自然。有人指着正在分“趟子”的生产队长说,是不是他闺女?大家笑得捂肚子,你捅他一锤,他拧你一把,扭作一团。
生产队长(我十岁时的那个生产队长不知什么原因叫人揍了一顿赌气不干了)分出“趟子”,“趟子”是根据人头平均分的,谁割完谁歇歇。几个老娘们叽叽喳喳不愿意,说,分得不公平。生产队长说,你跟你男人睡一张床上公平吗?那几个老娘们挨了骂,却痛痛快快地割起了麦子,嘻嘻哈哈的。割麦子的那块地叫“小泥湖”,土质好,夜潮,大旱天照样长出很有出息的庄稼。
麦子长得整整齐齐,一色的黄。麦秸粗壮而又密集,硕大的穗子很张扬地东张西望,累了的,弯了脖子,耷拉着头,就是熟掉了头的样子。坚硬的麦芒子带着刺儿,手一碰便会扎进皮肉。地里没有风,天上也没有风,铸造厂里的烟囱冒出的烟笔直笔直。几片不成气候的云彩无精打采,见到太阳躲得远远的,一会儿没了踪影。太阳直射进麦地,把麦香与潮气混搅在一起,浓得吸进鼻子都发粘。
大家一字摆开阵势,从北往南,挥起镰刀。我往手上吐了两口唾沫——这样捉镰刀把牢靠——学着大家的样子,挥舞起磨得锃亮的镰刀。而且我还带了一块磨石,随时准备镰刀钝了磨一磨。渐渐地,我被大家落到了后头。坚持到一半,我就倒在了地上,腰疼得直不起来。“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白居易割麦子疼不疼?
太阳毫不留情地炙烤着汗流浃背的我。我的表情只有一个:咬牙咧嘴。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其它能力来实施对抗,能做的只是把席荚子盖在脸上,阻挡日光的强烈照射。都说哪里磕倒了哪里爬起来,可我没有丝毫的能力。眼睁睁地看着大家以优雅的姿势在麦田里舞蹈,一片一片的麦子纷纷倒下。我默默地欣赏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镰刀挥起处,寒光一闪,拦住一大片麦子,往怀里一搂,麦子们便轻柔地依偎在挥镰者的怀里,还没来得及撒娇,就被摊在了地上。几个动作之后,挥镰者看也不看,顺手抽出一缕麦子打好“腰子”,两手握住“腰子”的两端,像抱孩子似的,准确而又麻利地把散摊在地上的麦子捆成麦个子,竖起来,往地上一杵,麦个子便坚定不移地矗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挥镰者又继续把镰刀的寒光娴熟地抛出去……没有人说话,连喘息的声音也听不见,只有镰刀撞击麦秸的声音在田间地头清脆地萦绕。
记工员韩芝云割麦子像一阵风。她割完自己的“趟子”,从地的那端给我接“趟子”。韩芝云大我四五岁,她家跟俺家隔着一条大街。我叫她三姐。接我“趟子”的还有一个叫李如玉的,也大我四五岁,我管他叫二哥。按说,他们接我的“趟子”,应当把我的工分劈给他们一些。但他们说什么也不劈。
三
1982年,生产队撤销,土地分到了家家户户。我们家分到了一块湖地。因为是湖地,土壤油水大,粪水足,麦子长势喜人。站在地头,放眼望去,一片金黄。心中感慨: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麦子,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
我太爷爷乃至我老爷爷的时候,我们家里是有地的。只是那时候的地是由佃户租种的。自从爱戏如痴的富二代的我老爷爷李节养了一支戏班子,地就越来越少了。我老爷爷被称为“节爷”的时候,粮食也越来越少了。“节爷”的称谓是用内心的怜悯和家里的粮食换来的。
一亩三分地在小河湾家后。过了南大桥,顺着河沿往南走不远,再沿着布满土疙瘩的小路往东走,觉得有些喘了,就到了。
父亲、我、二弟,一人攥着一把镰刀,按高矮个,前后有序地走着。魁梧的父亲走在前边,伟岸的身影让我既自豪又安全。父亲老是跟很多人打招呼,也不嫌麻煩。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些看上去明显比父亲年龄大的人,见了父亲恭恭敬敬“喊四叔”。不管见了谁,父亲总是显得彬彬有礼,不见丝毫的懈怠。父亲平常也是这样,有一次,下了班的父亲骑着自行车,遇见一个青年,依然下了自行车跟他打招呼。那青年慌慌忙忙地说,舅爷爷舅爷爷你别这样,你这样我还得给你下跪吗?
我从小就有走路不抬头的习惯,娘说,低头低得背都驼了。二弟是一根拉拉秧就能挂住的主儿,一路上什么都碍他的事儿,不是把路边的树枝子压弯了再弹起来,就是一脚将土坷垃踢出八丈远。终于老实了,是因为他的手里多了一只青蛙。
疙疙瘩瘩的阡陌小路上,装满麦个子的地排车独轮小轿车不厌其烦地颠簸着。路窄车多,相向错车时,就会有粗野的吵骂声蔓延在麦田里。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就会将对方的车子推进路边的水沟里。吵骂停止,弱者忙着跳进水沟里捞麦个子。天热脾气大,累了脾气也大。又热又累,就容易发作。
按照三二一的比例,我们父子三人分好“趟子”,各自不声不响地割起了麦子。
割完麦子,父亲回家借地排车。刚分地那会儿,很多家庭农具设备不齐全,用的时候就指望借。父亲临走的时候,吩咐我和二弟把地里的麦个子转移到地头路边,回来装车方便。父亲前脚走了,二弟就不干了,坐在地头玩。我喊他,他答应着,就是坐在地头不动弹,像是腚上长了钉子钉在地上了。转了一会儿麦个子,我也累了,刚在地头土埂子坐下歇歇,二弟拍拍腚起来了,一溜小跑到地里抱麦个子。这还差不多,我想,一人干一会儿,歇一会儿,也算公道。正得意着,只听得屁股上“咚”的一声,吓得我拍拍腚跳起来。
满头大汗的父亲像关公,气哼哼地说,还坐,太阳都快上宿了!我本能地看看太阳,刚刚偏西。再一转头,二弟正一本正经地往地头抱麦个子。我恍然大悟,父亲是嫌我光歇歇不干活,只有二弟一个人在干。现在想想,哪座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呀!事后说起,父亲笑笑不语,二弟洋洋得意。
麦子收回家,堆放在打麦场不远处,连夜排队挨号,一直要到下半夜才挨上。脱粒机白天晚上连轴转,一阵阵翻江倒海,把一个个麦个子分解成麦穰、麦糠和麦粒。收拾完了,虽已疲惫不堪也要骑上自行车直奔糁铺。两碗牛肉糁,五个驴蹄子烧饼,吃饱喝足,晃悠到南坝桥头,跳进水里泡上一阵子。回到家,老婆问,吃饱了吗?答曰:五个烧饼两碗糁,只觉水珠没打牙。
我居住的城市在变魔术似的一天天长大,我的农村老家也在日新月异地朝着城镇化发展。原来的麦田不见了,规划了,建设了,高楼大厦代替了清明过后的麦苗,节节拔高。日子也在节节拔高。超市广场代替了接踵比肩的集市,熙熙攘攘。日子也在熙熙攘攘。
没有地种了,越发怀念起麦收的日子。
起身,轻轻掸拭摆放在书橱上的《拾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