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萌萌《比雪更冷的家书》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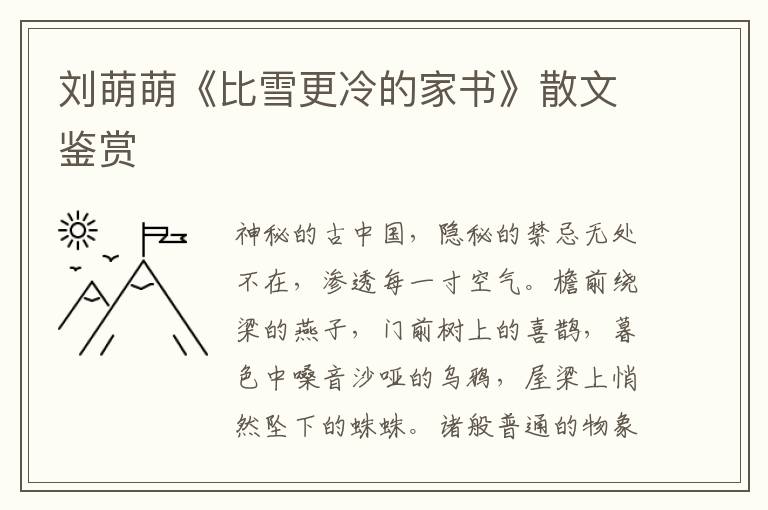
神秘的古中国,隐秘的禁忌无处不在,渗透每一寸空气。檐前绕梁的燕子,门前树上的喜鹊,暮色中嗓音沙哑的乌鸦,屋梁上悄然坠下的蛛蛛。诸般普通的物象之下,潜藏某种暗示和预言。在“坐月子”这件事上,更是忌讳多多。女人生育不能在娘家,否则引来血光之灾,若有兄弟,必又招来恶声恶气:女人在娘家生养,手足兄弟将一生落魄潦倒,俗语说,“穷得打铁”。母亲无兄无弟,却也并非福音乐事。母亲八岁时外祖母病逝,外公后来又去了遥远的别处,遥远的不仅是地域,更在时间与内心,以及整个时代余响回旋的寒凉境遇。昔年的老宅早被充公,作为徒有其表的外壳,房子坚固地矗立原地多年,房子的灵魂,“家”的气息和意义却在蒙尘的时间里散尽。是这样的背景之下,母亲嫁给父亲;是这样的背景之下,她还能有怎样安逸的月子可以指望?老妇们啰里啰唆,笃信相沿的经验,包括宁信其有的道听途说。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她们凭着母性的灵敏嗅觉搞到红糖、鸡蛋这些稀缺的补品。产妇的头发油腻腻的,打着络儿,从包着头巾的鬓角垂挂下来——是的,不沐不簪。头不能梳脸不能洗,以防感染风寒,脚趾甲不能剪,牙齿更不能刷。老妇们上了年纪,絮絮叨叨,扯著母亲的衣袖,把一生的经验悉数倒出。饥荒年月,同情也是抚慰的一种。
多年后,对门的媳妇生了小孩,母亲去探望,两罐香浓的麦乳精和奶粉,还给小孩子扯了块柔软的花布。我对生孩子一知半解,约略知道从女人的肚子里取出。听说有了进口的羊肠线,随着伤口的愈合融入血肉,免却拆线之苦。母亲赞叹医学进步神速,女人们因此少遭多少罪呢。怎么还遭罪呢?不是说,生孩子是喜事么。我狐疑地跟在母亲身后,掀开门帘,走入产妇坐月子的房间。母亲叮嘱,婴儿太娇嫩了,除了他的母亲,谁都不能触碰。我不靠前儿,倚在门框上,远远儿地看。产妇的头上包着白帽,丰腴的上半身倚住棉被,满足的脸上挂着歉意似的微笑,撩起一角的衣襟下,拱着婴儿的头。这个闭着眼睛的怪物吮吸出叭嗒叭嗒的响声,好像饿了很久。屋内热气烘人,草编炕席的味道混和婴儿身上的乳香,每个人的神情又开心又隆重,明崭崭的光线里,大家仿佛喜获新生。
祖母没有为我的到来备下一件薄衫。母亲决定亲手缝制。单的,棉的,衣服,小被子,以旧翻新,哪一件都得她亲自来。偏偏这时候,村子里死了人。诚惶诚恐的众人收起针线,纷纷把手拱入袖笼。村庄里通行隐秘的忌讳:倘有人亡故,一月之内不得动针线。违拗禁忌的人家,难逃穿针引线般接连死人的灾祸。母亲身怀六甲,镇定如帐前的将军,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做了棉的做单的,缝了大的缝小的,对于流传已久的禁忌视若罔闻。不能不说我家屋后那块巨大的石碾。先时,人们背来自家的稻谷,放在扇形的磨盘上,男人们张开粗壮的臂膊,推着石碾虎虎生风,一圈,又一圈儿。直到稻子或谷物脱落硬壳,留下细腻的面粉或晶莹的米粒。然而,这块沉重的碾盘占据的土地被村人视为不祥,不宜动土盖房。然而,父亲笨拙的唇舌和他卑微贫困的地位,无力说服村庄权力的掌握者,恩赐我们另一块土地。最终,我们将房子盖在了磨盘的前面。磨盘弃置多年,人们依然心有芥蒂,为居住在房子里的人而担忧。值得庆幸,我们躲过乡村里种种诡异的说法,平平安安活了下来。回望那段岁月,无论猫腰塌背,还是昂然而行,谨慎而莽撞的姿态和一溜小跑穿过割人肌肤的高粱地没什么两样,一味向前外,再无别法。
我出生没几天,传来祖父卧病的消息。大姑在信上保持生活中一贯的态度,淡言淡语而又不容余地:父亲要么留下来伺候母亲的月子,要么去照顾生病的祖父,何去何从,自己掂量权衡吧。至此,祖母的形象和五个女儿叠印一处,炯炯的目光透过纸背,注视父亲的一举一动。那样的目光有着丰富的内涵、锋利的霜刃,犹如麦子的尖芒,泛着寒意的镰刀,随时准备收割父亲疼痛的良心。父亲感觉心脏在慢慢变冷,缩紧。他结婚刚刚一年,羞涩而虚弱的内心,哪经受得住老辣的祖母鹰隼般锐利目光的检视,更何谈妄图从她肥大的对襟棉袄下挣脱。从一开始,祖母表现得就像一个勤勉的铁匠,叮叮当当,话里话外时时敲打。诸如:媳妇是窗户纸,破了再糊一层。去了红的来绿的。两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到处有。露骨而又匪夷所思的说辞,像剜入骨髓的小刀,极尽曲折,把母亲从父亲和他身后的家庭中一点点割离出来。
“月子”——女人一生中意义重大的段落,交待先人,延续后人。家族中性情各异的女人们似浮萍如游鱼,各自散落不同的地域,至此而环环相扣水乳交融。有钱人家燕窝鱼翅,贫苦人家鸡蛋挂面,几句嘘寒问暖的话,于产妇同有滋补之效慰藉之功。作为刘氏媳妇的一员,母亲一步步走到她的月子里。我惊讶地睁大眼睛,发现那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除了大把的寒冷和空虚。月亮从四十年前的夜晚投下一地清光,笔直,坚硬,盈盈如积雪。母亲躺在冰凉的榻上,她的身下,一席之隔,是冰冷、坚硬的土坯,寂灭的炕道里,回旋着的冷风取代了温暖的火焰。茫然的目光汲取了清冷的寒意,雪色的反光。既是虚弱的产妇,又是仅存的劳力,厨房和尿布兼顾。父亲留下借来的五个鸡蛋、三包挂面。这是产妇一个月的吃喝用度。或者说,是我们两个的。她像捧着易碎的鸡蛋,小心地把我搂入肘弯,贴着温暖的胸口和柔软的小腹。她很快发现,这个小东西比想象得麻烦得多。像一块烫手的山芋,不安分地在她怀里颠来倒去。热汗渐渐渗出母亲的额头。她变着法子安慰我,希望我安静下来,哪怕就那么一会儿。不懂事的婴儿没头没脑,在饥饿和寒冷中哭闹不停,在她四处漏风的月子里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
回忆赋予我神奇的能力。我轻而易举攀上时间的枝巅,像探头探脑的鸟俯瞰人间的低处:走出家门的父亲仿佛苍茫天地间一枚肃肃宵征、奔波在途的孤单小吏,又如得到传令的兵士,心底忧愁烦闷,腿上却抖擞精神,一刻不敢耽搁地赶往祖父的病榻。寒天冻地,父亲穿的还是秋天的绿胶鞋,其中一只大脚趾顶出了破洞。他一点都不感觉到冷,一路小跑,头顶甚至冒出隐隐的热气。火车一声长啸。茫茫白雪般的蒸汽,关山飞度——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疾驰的车轮飞速而缓慢地碾过一个又一个站名。透过母亲的讲述,我看到四十年前绿皮火车的车窗上,映现出年轻父亲疲惫而迷茫的脸。读《西游记》,无论唐僧的紧箍咒还是三清道人的乾坤袋,我都坚信绝非凭空杜撰。吴承恩一定在生活中验见过那种无可违拗的伟力,如同父亲,一脸忧愁地面对传唤他的一纸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