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朝晖《海棠花事知多少》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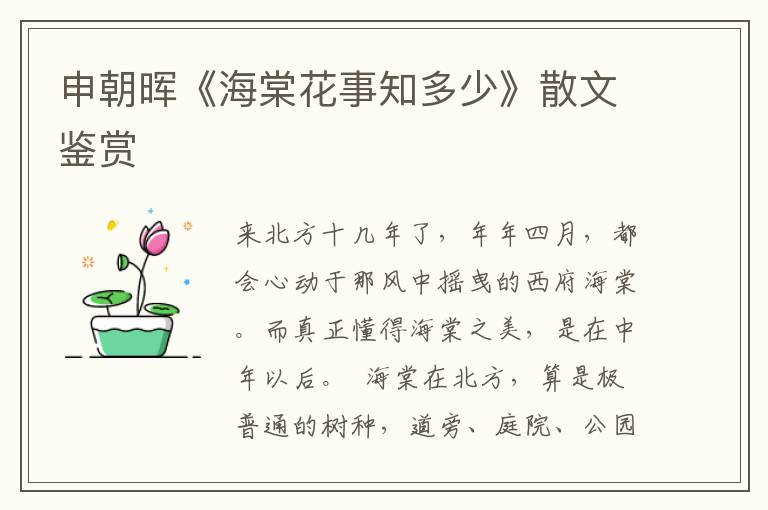
来北方十几年了,年年四月,都会心动于那风中摇曳的西府海棠。而真正懂得海棠之美,是在中年以后。
海棠在北方,算是极普通的树种,道旁、庭院、公园、山丘,随处可见。我上班必经的路上,有两排西府海棠,因为树种大小不一,花期早早晚晚能开上小半个春天。海棠树高高的,枝叶疏朗,花开时,花叶齐生,相互掩映。坐在公车里,也能清楚看到。花期盛时,只要时间空闲,我常常愿意提前下公车,漫步走过那条海棠盛开的街道,去享受那满树的繁华,和繁华背后淡淡的清寂。
赏花亦需机缘。花海茫茫,首先得遇着你心动的那一种。譬如季羡林先生写过《二月兰》,也写过《海棠》。但细读便知,他写二月兰时有无限的深情,在花的观照里浸透着自己的人生足迹。而他笔下的海棠,无疑干涩得多,诚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虽然喜欢海棠花,却与海棠花无缘。其实即便是有缘,若做到花人两相和,还待因缘际会。
十几年前,刚出校门,为了爱情,无犹疑地只身来到北方。记得初遇海棠花的那个春天,惊异于这长长的花梗,且发现这花的颜色开得递次,带骨朵的色泽深粉,花瓣绽放便开成了粉白,只花瓣的边缘和背面还藏着绯红的底子。在我上课教室的廊前,有一株海棠,有时我也会突发联想,折几枝带到教室,开瓶矿泉水插上,让学生当静物描写。那时也迷惑于张爱玲所谓“人生三大恨事”中“海棠无香”的正确性,因为这花就摆在我们面前,香气袭人。后来才知道海棠花分四品:贴梗、垂丝、木瓜和西府,唯西府海棠是有香气的。传说西晋大富豪石崇一生极爱海棠,在洛阳建了别院金谷园,园内尽植海棠,逢春必叹:“若使海棠能香,当铸金屋以藏。”洛阳地处中原,西府海棠耐寒,多生黄河以北,多才多金的石崇大约也不知佳人原来在水一方。
海棠开在百花深处,却自有英气。她不似梅菊,独立霜枝,有意拉开自己与群花的距离,以获得那份物以稀为贵的尊荣。她也不似迎春、山茶,要拔得头筹,俏立春寒。她没有桃花的娇艳,没有丁香的馥郁,在枝叶花影的疏朗中,她有一种自在云天的美。朱自清在《看花》中写道:“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百花之中能将繁淡处理得如此恰当的,大约也只有西府海棠了。春花灿烂,开得繁的花树满园都是,如早春的桃花、樱花或紫荆,常常是老树新开,一串串,一簇簇,贴着枝桠,挤挤挨挨,灿烂得像一株瓶插。西府海棠树高枝阔,每一个花骨朵上都有长长的花柄,在绿叶的掩映下,满树繁花,却没有簇拥之嫌;再加之花色清雅,故这满树繁花的海棠又独独多了一些百花没有的英气与清寂了。
都说海棠能雅俗共享。历代文人多以海棠喻美人,这美人之美大约也不同于“人面桃花相映红”中的美了。唐明皇把杨贵妃醉后未醒的酣态比作“海棠睡未足也”。苏轼在《海棠》一诗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算是对这一意象的承继。但东坡对海棠之爱绝不停留于此。1079年,43歲的苏轼被贬黄州,寓居在定惠寺之东,发现东岭小山有一株海棠,极为兴奋,写下了一首题为《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据说此诗被苏轼自视为“吾平生最得意诗也”(《王直方诗话》),每每写以赠人。而在散文《记游定惠院》,他也写道“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至此,苏轼在海棠中约摸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可怜的美人影子了,那句“土人不知贵”分明也在说他自己的人生境遇。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却也能随遇而安,这与生在百花丛中却能自带英气的海棠一样,游走在繁华与清寂的边缘,自在云天。
在北京赏海棠的地方很多,城区最美的应是元大都遗址公园的小月河两岸,沿河弯流经安贞门的地方,有一处海棠花溪,每到四月,游人如织。此处海棠树高而密,绕水而生,仰首可赏繁花似锦的春之灿烂,低眉却又见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另一种幽境。而我却独爱那散落在道边或小院的一两株海棠,信步走过,不早不晚刚好遇见她满树繁花,你就静静在花树前站站,小憩一会儿,听风中细语,听花叶静静绽放的声音,那一刻,这城市的喧嚣像遁去了一般,你在刹那与永恒中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音,而后,你转身消失在人海深处。
在繁华与清寂的人生边上,我愿开落成一株海棠,即便人生注定要雨疏风骤、绿肥红瘦,我也愿在心底守住那片海棠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