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亚《摇曳的黑白光影》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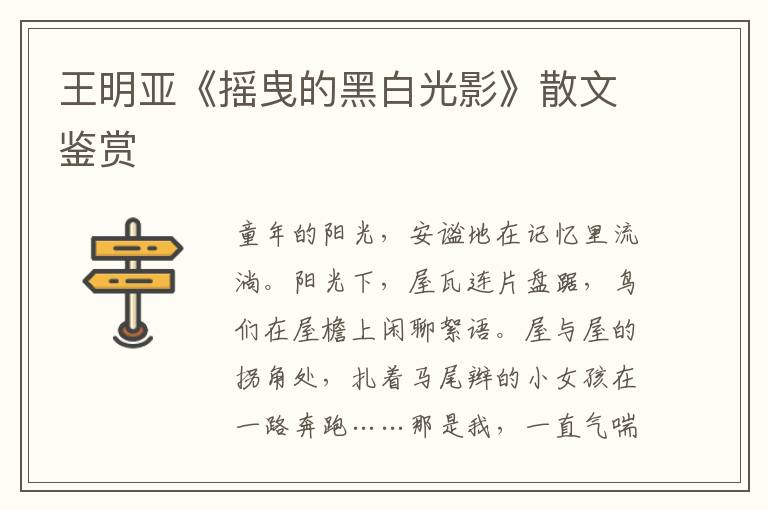
童年的阳光,安谧地在记忆里流淌。阳光下,屋瓦连片盘踞,鸟们在屋檐上闲聊絮语。屋与屋的拐角处,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在一路奔跑……那是我,一直气喘吁吁地跑到今天,带来很多旧光阴的味道。我看着那些安息在旧光阴里的人和事,看着看着,呵呵,不禁笑出声来,或者,呜呜地淌出泪来。但我仍然相信,旧光阴是有营养有色彩的。
那是一只墨绿的煤油灯,敦实的底座,浑圆的肚子,细长的脖颈,婷婷然立在壁柜上,立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黑夜里,棉制的芯火摇曳着,半明,半暗。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只灯盏了。因为突然有一天,这只烟熏火燎的煤油灯“嚓”地一下被一只灯泡捻灭——我们村通电了。我家15W的灯泡像一只眼睛安然地悬挂在旧椽梁上,我们欢喜地拉扯门角的电绳开关,呯,亮了,呯,熄了,神奇得不得了。一熄一亮之间,日子也像一盏橘黄的灯有了温度。——这是黑暗和光明的过渡。是过去和未来的过渡。
让人更欢腾雀跃的是,我们村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放在邻居狗爷家。9英寸,看上去就像个小箱子,里面却藏着一个神奇缤纷的世界。六岁左右的我,记忆也像灯泡一熄一亮,有了很多的明明暗暗。
那时大人总说:不听话今晚就不带你去看电视了。那可不行,无论如何也要挤在人群里,闪着童稚的大眼睛,一眼一眼地看稀奇,凑热闹。那气氛,活跃了一村的男女老少。堂叔堂姑们大一些,他们十多岁,放了学,回到家,书包一扔,赶着做作业,然后抓紧时间做饭吃饭洗碗喂猪食。农忙季节,割稻插秧收谷子,一路都在跑。他们动作敏捷利索,一改白天的懒散。因为这个时候狗爷家的电视广告音量正穿过屋瓦高分贝地喊叫着。
那是些照亮我们生命底色的广告:洗白牙齿的田七牙膏、光洁亮丽的白猫洗衣粉、活泼动感的燕舞收录机、酷烈强劲的来福灵农药……,听起来都生动迷人。那些广告词老少皆熟。如燕舞收录机: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如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来福灵农药: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我们在这些广告产品的更新换代里成长着。随后有了威力牌洗衣机:威力威力,够威够力,省优、部优、国优……每一个广告明星,他们的动作、声音、宣传的产品,都成为农村黑白世界里的传奇和经典。大孩子们一天到晚扭着屁股唱“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小孩子们则举起双手喊“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他们的大人瞅着不高兴了,“啪”地劈一巴掌,斥道:不知道帮大人干活,害人精。大人虽然买不起威力牌洗衣机,也会不时冒出一句“省优、部优、国优”。
广告卖完就是正片了。昨天看到精彩的部分没有了,正等着续上呢。如果偏偏大人不让去,对正要扯开腿跑的孩子怒喝:给老子倒盆洗脚水来!要命的是:把那盆猪草剁了再去!孩子顿时又回到没有电灯的时代——呜呜,一盆猪草剁完,别说广告没有了,正片都放完了。于是撅着脚掉眼泪。大人凶的,孩子既不敢哭,也不敢动脚,老老实实守在猪草盆边,抓着铡刀乱剁,嗵嗵嗵,像剁他纷乱的思绪,眼睛又不忘斜视着正从他面前跑过去的同伴。见孩子这般光景,有的大人就不耐烦地朝孩子挥手:去去去,看得老子心里起火。孩子不敢抬头看大人的脸,只杵了一下,撒腿就跑。
其实大人看电视比孩子更走心,他们常常在田间地头拿某个漂亮的女演员说荤话,轰地爆笑一地。或者争论故事情节发展,有时意见不一,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之后闷头干活,决定晚上看了续集再分高低。这点精神想望,或对某个演员的迷恋,丰盈了他们贫乏的生活。当听到广告像喇叭在喊他们时,心里自然也是急的,只是不像孩子表现得那么躁动,时间他们掐得准着呢。也有不靠谱的大人,黄昏从地里回来,挑着庄稼,路过台堤,看见狗爷家已经人潮攒动,他就放下担子挤进来,看得嘻嘻哈哈,忘了他还有一担庄稼在堤上。有的把牛绊在河边的树桩上,等看完电视再牵着牛回家,真是晚归的牛人。
大人们也像孩子一样,最爱看武打片,嘿嘿哈哈,打打杀杀,如《霍元甲》《霍东阁》《陈真》《八仙过海》《再向虎山行》等等,仿佛能从中学得一些功夫。没读过书的农民,听不懂电视里的普通话,只是盯着9英寸里的小人儿动来动去,说一些“啊,那个人要掉出来了”的傻话。或有的人不时从嘴里发出“滋滋”的吸溜声,仿佛哪一拳正好砸在他的脑门上,他疼得肝胆俱裂。剧里的爱情也是很迷人的,假若他们喜欢的两个人没有在一起,他们便会一片唏嘘,甚至咒骂,好像是他们自己失恋了,或者他们隐隐想要的爱情不过也是个破产的银行,就沉默不语了。有时看着看着,收视信号突然不好了,电视上又正好在比武,屏幕上却跳荡着条条杠杠,或闪烁着密密麻麻的雪花点。狗爷扑过去摇天线,前后左右摇了个遍还是不顶事,只听到里面打得热火朝天。脾气暴躁的人就大声骂:把电视机都打烂了!大人小孩也是急得一片哗声。
狗爷家屋子小,若是天晴,他就把电视机挪到大门口,门前就挤得水泄不通;如果下雨,他们家的堂屋简直要被挤炸,屋里还弄得水一脚泥一脚。看电视的时候也是各抒己见,孩子更是禁不住嘴,一场电视看下来,实在躁得慌。狗爷就开始讨嫌这么多人了,尤其孩子。
我常常蹦跳着跟在堂叔他们后面。堂叔他们想看电视也是有活儿要做的,狗爷先支使他们剁猪草、挑水、洗碗、收谷子、扫地,遇什么干什么。我常负责照看他的两个小小孩,给他们喂饭,陪玩。只有狗爷家的活儿干完了,他才会大着步子进屋开电视。这时,大人小孩早把屋子挤得密不透风。有的人挤不进来,就趴在墙外的窗户边往里瞅,除了密实的脑袋,天知道他能瞅到什么。不管看什么,狗爷都不许我们讲话。他个子高大,粗眉竖眼,脾气差,语气重,一出声,够瘆人的,直把我们兴奋的劲儿压下去。我不懂事,经常看着看着突然高声嚷嚷:呀,打死他!打死他!狗爷就一眼横过来,吓得我缩成一只小乌龟。可是一会儿我又忘形地叫出声来,或一口涎水吐在地上。狗爷忍无可忍了,一把拎起我的瘦胳膊往门外搡。我就哭着回家。母親很是愠怒:叫你不要去看你硬要去,嫌你了吧?不去看了,明天不许你去。母亲的确就不去看电视。可我是小孩子呀,哭了今天,明天又忘了。
后来,1985年秋,一天放学后,我们的父亲突然对我们说:我们家买电视机啦。
我们果然就看见父亲在堂屋里摆弄着一台崭新的电视机,也是黑白,但是,那可是14英寸呀!比狗爷家的电视机大了5英寸!而且,这还是我们村第一台私人电视机呢,是父亲卖了猪和花生后花480块钱买回来的。消息立刻轰动了整个王庄。这天晚上,来我们家看电视的人络绎不绝,门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我们几个小屁孩神气得不得了,给来人搬椅子,倒水,忙得不亦乐乎。那些来看电视的人,得了这样的款待,高兴地从口袋里掏一把蚕豆或花生给我们吃。狗爷家相比可就冷清了。之后,我们再不用提心吊胆地去狗爷家看电视了,而且可以一直看到电视机闪雪花,这样的后果是上课打瞌睡。有一次高老师扔过一支粉笔,刚好砸中我酣睡的鼻头。我忽地一下站起来,立即惹来哄堂大笑。高老师说:听说你家买了电视机,你告诉我昨天晚上演什么?我当真说起《萍踪侠影录》里的人物和情节来,其中劉松仁演的张丹枫可是我的偶像,我说得头头是道。说完,抬头看高老师,他一脸愠怒,喝道:明天起你不用上学了,就在家看电视。可是……他不是也听得津津有味吗?更奇葩的是,第二天课间,他悄悄问我:那个张丹枫演到哪里了?我一脸懵相。
有14英寸电视机的那段时光,是我们家最鼎世的繁华了。之后,村里陆续有了很多电视机,不再像以前挤到别人家一起看,一起讨论,一起争吵。那个年代的电视机里,我们看了很多记忆深刻的好片子,有《射雕英雄传》《济公》《西游记》《红楼梦》《刘胡兰》《英雄儿女》等,还有《唐老鸭与米老鼠》《聪明一休》等动画片。春晚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很多深入人心的歌曲从春晚的舞台飘出来:《幸福在哪里》《军港之夜》《血染的风采》《我的中国心》《爱的奉献》《冬天里的一把火》《鲁冰花》……在依然贫瘠的乡村,这些歌曲像一盏盏灯,照亮我们灰暗生命里的旮旮旯旯,点燃我们内心深处蠢蠢欲动的梦想。
后来我们家也不知道换了多少台电视机,直至如今的彩色液晶智能电视,55寸,薄薄的机屏霸气地贴在墙上,遥控器随便一点,上百个频道任你遨游。父亲却常说没什么好看,歌儿也没什么好听。我想起从前看的那些电视剧,听的那些歌儿,还有那些贴近生活的广告。因此问父亲,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后来去了哪?父亲怔了一下说,那哪还记得?应该是不中用后当废品卖了。我又感叹,狗爷家那台公家的9英寸电视机也应该早就没影了。
父亲没有作声,只意味深长地望着院子前方,眼神落处,正好是狗爷家的屋顶。那自然也不是旧时的屋顶了,这儿小楼兀立,琉璃亮瓦,阳光塑金。那儿,我们看到的却是上世纪80年代的黑白时光,狗爷家的土房素瓦,震天的广告语音穿屋而出……也许父亲看到的是他壮年时最艰苦也最丰满的岁月。我看到的,仍然是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她正顺着房屋的拐角处兴奋地朝狗爷家奔跑。屋檐上,一线柔和的黑白光影正沥沥摇曳着……我不禁抿嘴而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