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战国兵法·孟子》原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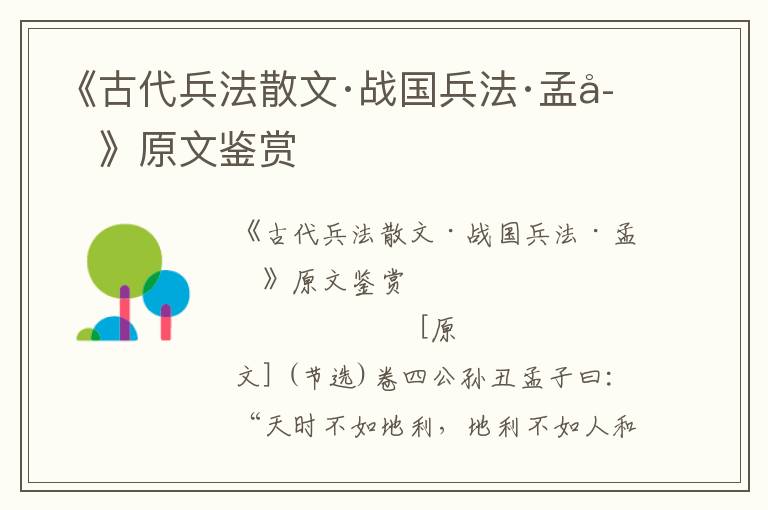
《古代兵法散文·战国兵法·孟子》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卷四
公孙丑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恩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 是何言也! 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侯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 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 于宋,馈七十镒而受; 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 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
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孟子谓蚳氏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蚳氏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
齐人曰:“所以为蚳氏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氏为辅行。王氏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 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
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於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忠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 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 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 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之。”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恶! 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
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 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 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 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 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 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 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 予日望之!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 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 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鉴赏]
《孟子》,儒家经典之一。战国时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著。也有人认为是孟子弟子、再传弟子的记录;还有人认为《孟子》是孟轲自己著成。《汉书·艺文志》著录11篇,现存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共7篇。相传另有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外书”4篇,现已佚。《孟子》一书问世后,其地位逐步提高。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在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一度任齐宣王客卿。因主张不见用,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后来宋儒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的记载。他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 认定残暴之君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极力主张“法先王”、“行仁政”,恢复井田制度,省刑薄赋,达到“黎民不饥不寒”,以缓和阶级矛盾。肯定人性生来是善的,都具有仁、义、礼、智等天赋道德意识。提出有所谓“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但也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认为“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教人注重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还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对后世很有影响。由上所见,孟子虽然自以为是孔子之学的继承者,但因为时代已经相距百把年,形势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孟子对孔子学说不但有所取舍,而且有所发展。
首先,孟子和孔子之论“天”稍有不同。“天”的意义,一般有三、四种。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义理之天,一是主宰之天,一是命运之天。孟子讲“天”,除“天子”“天下”等双音词外,连“天时”“天位”“天爵”等在内,不过八十多次。其中有自然之天,如:“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孟子·梁惠王上》,“天之高也”(《孟子·离娄下》)。有义理之天,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下》)。有命运之天,如:“若夫成功,则天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上》)。却没有主宰之天。在孟子中还有一种意义比较艰深的“天”,其实也是义理之天,或者意义更深远些,如:“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实质上,这种“天”,就是民意。孟子说得明白:“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中所谓“天吏”、“天位”、“天职”、“天禄”、“天爵”,都是这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在论语中所没有的。《论语》尧曰篇有“天禄”一词,和孟子“弗与食天禄也”意义有所不同。《论语》的“天禄”是指帝位,孟子的“天禄”是指应该给予贤者的俸禄,依它们的上下文一加比较,便可以看出其中的歧异。
孔子重视祭祀,孟子便不大多讲祭祀。论语仅一万二千七百字,“祭”字出现十四次;孟子有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多字, 为论语2.7倍强,“祭”字仅出现九次,“祭祀”出现二次,总共不过十一次,而且都未作主要论题。
第二,孔子讲“仁”,孟子则经常“仁义”并言。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孔子因为周武王以讨伐商纣而得到天下,谈论音乐,认为周武王的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孟子却不如此,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杀其君”,孟子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杀君也。”
孟子不但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还主张“贵戚之卿”可以废掉坏君,改立好君。孟子看君臣间的互相关系也比孔子有所前进。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孟子却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这种思想比后代某些“理学家”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高明而先进不知多少倍啦!
第三,孟子“道性善”。并且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承认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他承认事物各有客观规律,而且应该依照客观规律办事。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相传禹懂得水性,所以治水能成功。孟子认为一切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依客观规律办事,便是“行其所无事”而不“凿”。即使天高得无限,星辰远得无涯,只要能推求其“故”(客观规律),就在当时以后一千年内的冬至日,也可以在房中推算出来。
孟子的军事思想,源于他的政治理论。他反对各国之间的武力兼并,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孟子在《公孙丑下》篇解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时,引用攻城例子,来说明行仁政得天下的道理。“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就是说有一座小城,每边长仅三里,它的外郭也仅七里。敌人围攻它,而不能取胜。在长期围攻中,一定有合乎天时的战机,却不能取胜,这就是说得天时的不及占地利的。另一守城者,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甲胄不是不锐利和坚固,粮食不是不多;然而敌人一来,便弃城逃走,这就是说占地利的不及得人和的。所以我说,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行仁政的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的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都反对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都顺从他。拿全天下顺从的力量来攻打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仁君圣主或者不用战争,若用战争,是必然胜利的了。
《孟子》一书行二千多年而不废,必有他合理的内核,值得我们研究。但他的一味强调“仁义”,鼓吹井田制的政治主张,在当时七雄争战,富国强兵的背景下,显然是保守的,有的甚至是倒退的,需要我们正确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