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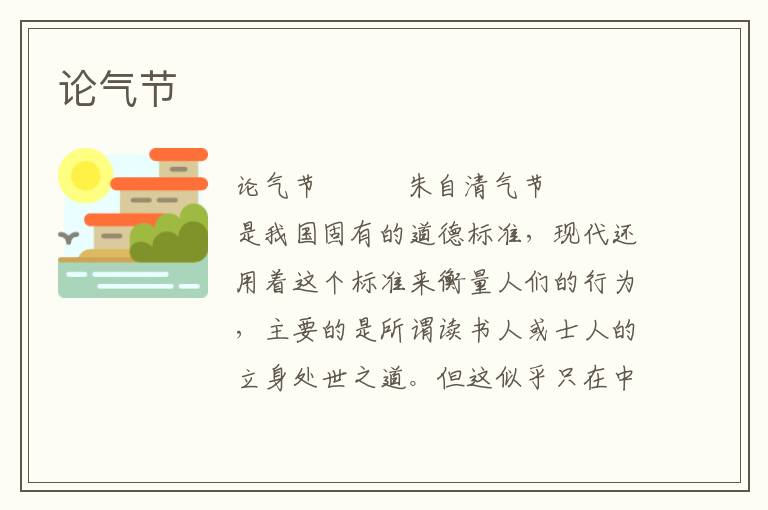
论气节
朱自清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GF8CF]]党”,“[[!GF8CF]]”是“[[!GF8CF]]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会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原载1947年5月1日《知识与生活》第2期
〔鉴赏〕 中国人历来重视气节,对文人尤其如此。如文章开头指出的,“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讲究“气节”的传统,在我国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其流风余韵至今仍然存在。毫无疑问,以天下为己任,谋求治国安邦,使自己成为济世之才,始终是士人的理想和抱负。曾参明确地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只是贪恋个人的荣华富贵,就不能算作是“士”了。孟子对“浩然之气”的描述说明了这一点:“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与“道”、“义”相配合的,一旦失去了“道义”,这股气就没有了。这里的“气”,类似通常讲的勇气,是指表现于实际行动中的精神力量。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上》),这样大无畏的品性,是从这里引申开来的。这种风习一直不绝如缕地流传下来。东汉末年的士人领袖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世说新语·德行》),其他如范蕃、范滂亦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党锢列传》)。北宋范仲淹的名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拨动过多少天下士子的心弦。明代东林党人那副脍炙人口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激起过多少天下士子的豪情。气节的本义是指志气和节操,后又有许多引申义,几乎一切美好的品德和行为都可以此来概括或纳入其中。譬如独立人格,大义凛然,迎难而上,不随波逐流,清廉勤政,犯颜直谏,忧道不忧贫,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敢于临危授命,舍生取义等。特别是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在敌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坚持正义、不怕牺牲的品质。在历史上,有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他们是讲气节的楷模。近现代的中国,更是涌现出无数的志士仁人。作者本人就被毛泽东视为讲气节的榜样。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又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里的“骨气”、“英雄气概”,说的都是气节。反之,像秦桧、汪精卫、周作人等,不能说他们没有学问,但他们不讲气节,没有人品,也就被人们所唾弃。从语词发生学角度,作者结合历史变动的实际状况,考察了“气节”的涵义及其变化:“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气”每每偏重于积极的行动,而“节”往往带有不犯上作乱的消极性。作者以为,“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同时指出,在我国历史上,气节之“士”有在朝为官的忠烈之士,也有逃避到山林之中的隐逸之士。这些分析,都是很有见地的。最早将“气”与“节”两字连用、组成一个新词的是司马迁。《史记·汲黯传》中说汲黯为人,“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我国古代把士、农、工、商统称为“四民”。“四民”中的“士”由于掌握着一定的知识,因努力程度、机遇、志趣、性格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士”的命运会与每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相呼应,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金榜题名、攀龙附凤享尽荣华富贵的;有隐居山林、清幽逍遥的;有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的;有历经坎坷最终才显达的;也有怀才不遇一生穷困潦倒不堪的。名称上有侠士、文士、寒士、隐士、名士、高士之分,但整体而言,“士”的精神在于讲气节。有些士虽身无官位,职位卑微或已遭贬谪,却仍然心忧庙堂和天下苍生;有些士少壮时放荡不羁,而暮年却大义凛然;有些士生平无奇,甚至乏善可陈,在社会动荡危亡时刻,能良心发现,挺身而出,或为民请命,力斗恶势力,或保家卫国,洒血疆场。随着时代的变化,大约自五四运动以后,传统意义上的士渐渐演变而成为今天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工作,对他们行为的评判就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标准。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知识阶层“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这是从当时的现实出发的。说到知识阶层若想有所作为的话,认为必须走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不能固守传统的“气节”观念,而代之以“正义感”。气节的某些合理因素,仍有被继承发扬的必要,不过应随着时代进步而重新作出解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气节,大抵是民族气节、革命气节,即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坚持正义和真理,在敌人面前不屈服的品质。一些恪守传统学术精神和富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也依然会赢得人们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