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母亲不听话》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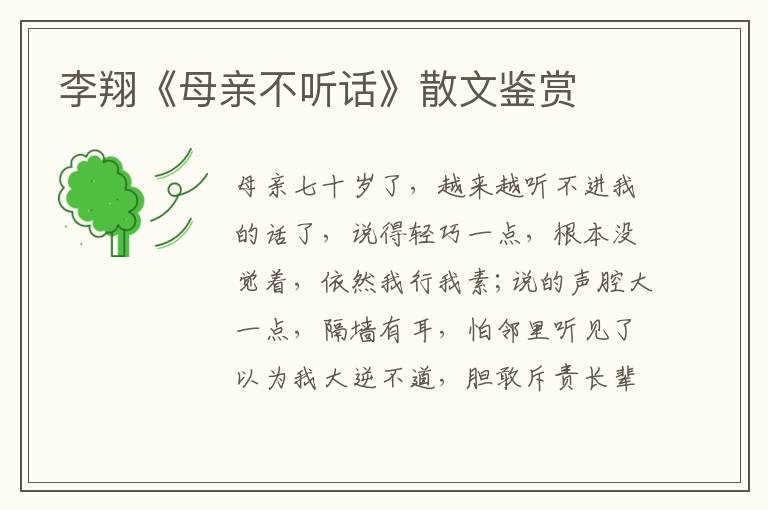
母亲七十岁了,越来越听不进我的话了,说得轻巧一点,根本没觉着,依然我行我素;说的声腔大一点,隔墙有耳,怕邻里听见了以为我大逆不道,胆敢斥责长辈;即使偶尔一声半语高了调门,过后亦是后悔不迭,愧疚难当。心里一遍一遍责备自己:“怎么能说母亲?怎么能说呢?母亲再不好也是至亲长辈,咋能由着儿子随意说道?亏你还是个读书人!”
就说前年春节吧。腊月里落了几场鸡爪雪,一层摞一层,到年三十也没消融干净,预料到天冷,路滑,跟前没个亲友照应,怎能心安?我提早泥了炉膛,换了崭新的铁皮烟囱,备齐了煤块,连燃炉子用的干柴禾也劈了一大堆码放在房檐底下。
临出门,我扳起指头叮咛母亲:“吃饭,睡觉,看电视,旁的啥事都甭管,记牢了。千万不要乱走,巷子口也别去,等天晴路好了再出门。”
“嘟囔八遍了,又不是聋子,把我当娃看哩,啥事我不知道,真是……”母亲愤愤的,显然有些烦我,“赶紧带娃走,要不天黑没班车了,甭记挂家里,我能照看好你爸和我。”
说这话是大年初三半晌午,我回老家给父母拜完年,要回城里的家了。可两天后的正月初五晚上,母亲却一路颠簸,从老家照金的小山村到了我所在的县城,躺在了骨科医院一张陌生的床板上,接受一位须眉皆白的年老医生怨气十足的治疗。我明白这是过年时节,大凡加班带点的都有些情绪吧。
“咋搞的?”医生看着片子上的裂纹直戳戳问。
“早上拉地畔上的杨树疙瘩,只连一点树皮么,那样难扯,一使劲,脚底打滑,跌个屁股蹲,右胳膊就垫在了石头上……”母亲强露笑颜,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娃们干啥去了,要你拉柴禾?”医生狠狠地瞟了我和妻子一眼,言下之意我们没照管好老人。
“怪我,怪我……不关娃的事,娃们把啥都预备好了,是我老糊涂了不听劝……”母亲怕我受了冤屈,尽管手疼,仍嘴角一抽一抽地替我抢白,“我嫌炉子太费煤,想拉那树根回来,剁成节子续着烧……你不知道,娃们刚刚买了房,手头紧,能省一点是一点,谁能料到这……嗨,运气瞎瞎的……今年运气瞎瞎的。”母亲懊悔不迭,话语挂了石头,沉甸甸的。
“哼!拉什么柴,胡成哩么(乱做事),害得人连年都过不好!”医生倔声倔气。我清楚医生话里的这个“人”不光是给他多加一个病人,我和妻子都包含在内。你想想,母亲病了,哪有儿女不在床前侍候的理儿?
母亲低了头,下巴挨在了胸腔上,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但嘴里仍有几分的不服,自顾自地嘀咕道:“谁知道跌跤呀么,要知道那样,还拉啥柴禾,给个金狮娃子都懒得拿,划不来么,又花钱又受疼的,唉!谁知道跌跤呀么……”
医生举着拍来的片子,左一眼右一眼端详着。我和妻子屏住气息,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不知那卦书样的片子写的是福还是祸。母亲抬了头,看那黑乎乎的布满了神秘的“塑料纸板”(片子)。但更多是盯着医生的脸,想从那纹路里搜寻到一丝半点的结果来,但医生一脸霜色,嘴闭得像上紧的啤酒盖,不撬是不会开的。
母亲猜不出个所以然,只好赔了小心,轻声问:“大夫,不要紧……是吧。”母亲故意弄出点大度和轻松。
“不要紧?你咋知道不要紧!要是迟来半天,麻烦就大得很了! ”医生似乎有点故弄玄虚,说话声震得片子呼啦响,“算你运气好,手腕骨折,打上石膏固定,在脖子上挂一个月再说。”
母亲紧张的眼神瞬间松懈了,像个扎破的气球,我和妻子的心“咚”的一下砸在地上。
打石膏之前先得正骨。正骨是通过牵引将脱臼的骨骼复位。这是个力气活,医生吩咐母亲站在病房中央,自己活动胳膊,挽起袖子,托着母亲的病手,稍稍一捏,母亲喉咙里“呀”一下。医生捏了捏,双手抓紧,稍一带力,母亲像个竹竿双脚拖拉着跟了过去。
“不行!人太瘦,没分量,轻得跟树叶一样。”“儿子上!”医生吩咐我在后面抱住母亲的腰。医生继续发力,母亲嘴里“咝咝”响,嘴角抽动着。我真不忍心将母亲拉来拽去,稍一泄气,母亲就成了风里的草,被医生拉得腳步踉跄。
“真是吃干饭的,小伙子么,没我个老汉劲大……媳妇呢?”医生扫视一眼妻子,“愣着干啥,去后面搭把手!”妻子早已不忍心再看,怎敢雪上加霜,唯唯诺诺,迟疑不前。
“别磨蹭,赶紧上,治病哩么,有啥好怕的!”
妻子经不住医生近似斥责的劝说,犹疑着转到我身后,搂住我的后腰。就这样,我、妻子,还有胖大的医生,将母亲夹在中间,四个人摆成长长的“一”字,六只蛮横有力的大手,将母亲瘦弱的身子狠命撕扯,让人想起年画上胖娃娃拔萝卜的场景。母亲脸白得像纸,没一点血色,有半边扭曲得变了形,但始终咬着牙,不吭声。
“一——二!用力!”医生竟然喊起了号子,“一——二!用力!”
我抱着稻草样的母亲,几乎要掉泪,一旁的孩子没见过场面,吓得跺脚扬手哭喊起来:“哇——别打奶奶,——别打我奶奶呀……”
总算复了位,医生给伤处涂了难闻的黄药水,打上惨白的石膏,一圈一圈缠上厚厚的纱布,用带子将那条受伤的胳膊揽着,绕过脖颈挂在前胸。这一只手算是被彻底幽禁了。母亲看上去成了十足的病人。吊瓶和口服药开了一大堆。我装包里背着,和妻子扶着母亲出了医院,一起坐车回了我城里的家。
“妈真是太犟了,不听旁人说,好好的受了伤,竟然还是右手,这下连吃饭上厕所都不方便了。”晚上,避开母亲,妻子有些怨言。
“老年人,都这样,想着为咱省钱哩,舍不得烧煤,拉扯树根,反倒贴了本。好心办了坏事情。幸好伤得不重,要是摔在腰上、腿上,弄不好一年半载下不了床,那才麻烦呢……咱多照看照看,很快会好起来的。”我安慰妻子。
“可不能再由着她了,要真像你说的那样,咱咋办,单位都这样忙,请假看脸色,谁来照应……反正得让妈记住这个教训才好。”
“对!得记住教训。”我看着妻子坚定地说。
打这以后,我和妻子得空就守在母亲身边说故事,而且挑的都是鲜活事例。
我从同乡嘴里得知,邻村有人摔伤,马上用一本正经的口气添油加醋地告诉母亲:“妈,后沟里根宝他妈,骨折了。”
“哟——啥时候摔的嘛?”母亲嘴巴张得像瓦窑。
“前天骨折的,半夜里打老鼠,摔了跤,伤了骨盆,还有大腿,医生说,年内甭想下炕!”
“唉——恓惶人,这可咋办呀,那个顶小的连媳妇还没娶上哩。”这个根宝他妈心肠极好,跟母亲分外相熟。母亲听了一脸忧戚:“还是怪她不小心,老鼠能糟践多少,吆喝一声不就跑了,犯得着赶来杀去的。这倒好,没吃上狗肉反倒连铁绳也搭上了。”
“就是的,就是的!”我和妻子一唱一和。
像这样的例子,我和妻子举了不下八例。都是有根有底,真人真事。母亲听得眉毛一皱一皱的,过了半晌,好像明白过味儿了,自顾自地嘀咕道:“谁知道跌跤呀么,要知道那样,还拉啥柴禾,给个金狮娃子都懒得拿,划不来么,又花钱又受疼的,唉!谁知道跌跤呀么……”
我知道,母亲在为自己的事而深感不安。心头不觉掠过一丝凄凉。
一月后,拆了纱布,去了石膏。医生叮嘱母亲右手不能太动,不能擀面条,不能提水桶,不能拎重物,至少要休养半年以上。即使彻底好了,也不能干太重的活儿。一定得小心为上。我和妻子留母亲再住了一段时间。母亲说啥也不肯留了,在客厅里转圈圈,唠叨家里的菜地荒了,唠叨那只芦花鸡胡乱下蛋,被狗娃娘捡了去,唠叨父亲一辈子没上过锅,几个月了,不知道咋糊弄吃的,熬坏了身子怎么好。
送母亲回了深山里的照金老家,临走时妻子反复叮咛。母亲这回没絮叨,她知道自己捅娄子给全家惹了麻烦,拉着孩子,看着我们,分外沉静地说:“俗话说,不跌跤,不长智,这回算是记到骨头里去了,不会再犯糊涂了,你们放心走吧。”话里透出少见的诚恳。
端午前的一天,母亲挑水时扭了腰,原因是多挑了几瓢水浇园子里的蔬菜。她想着自家的菜长得旺势了,省得到街上买,又是省一点是一点的想法作怪。怎奈人毕竟上了岁数,脚跟不稳,踉跄了一下,水桶滚到深沟里,扁担甩出去老远,人倒在了柴刺丛中。我们又气又急,轮番劝说。母亲痛定思痛,再次后悔。过一阵,又自顾自地轻声嘀咕:“谁知道跌跤呀么,要知道那样,还挑啥水,给个金狮娃子都懒得拿,划不来么,又花钱又受疼的,唉!谁知道跌跤呀么……”
去年,老家大拆迁,乡亲们四处投亲靠友寻住处。我将父亲母亲接到了城里,可他倆不习惯上下电梯,又嫌出门就是楼梯口,没个院子晒被褥。我见母亲过得不开心,在城边的王岩村租了两间小房子,让父亲母亲搬了过去。我隔三差五去看看,帮着买面、买米,料理料理生活。住这里水也方便,菜也方便,也有同龄的老人闲聊,母亲脸上的气色好了不少。可母亲毕竟知道城边花销大,愈加手细了。洗衣服的水不舍得倒,洗抹布,涮拖把。房间在二楼,室内楼梯,几乎透不进光线,大白天都难以看清楚台阶,母亲不管这些,上下楼梯扶着墙试探着走,很少开灯,就一次碰破了鼻子,一次崴了脚。过期的奶粉舍不得扔照样吃,腐烂的菜叶撕巴撕巴照样煮,洋芋冒出寸把长的青芽子剜巴剜巴刮了皮照旧炒一顿两顿。我和妻子一再劝说,母亲连连后悔,可就是说着忘着。
医生叮嘱过,母亲右手不能太过用力。父亲和母亲吃的面条、馍馍,都是在对门的菜店里买现成的。可当我去看他们时,总有擀细切薄的面条摆在案板上。母亲知道我自小喜欢吃宽面条,宁可忍着疼,冒着险,挪动病胳膊,也要为儿子擀出像样的吃食来。
端起热气腾腾的蓝沿儿瓷碗,挑着长长的筋道异常的面条,那一刻,我心里真是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
唉,我那不听话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