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迪思《游弋的骨头》散文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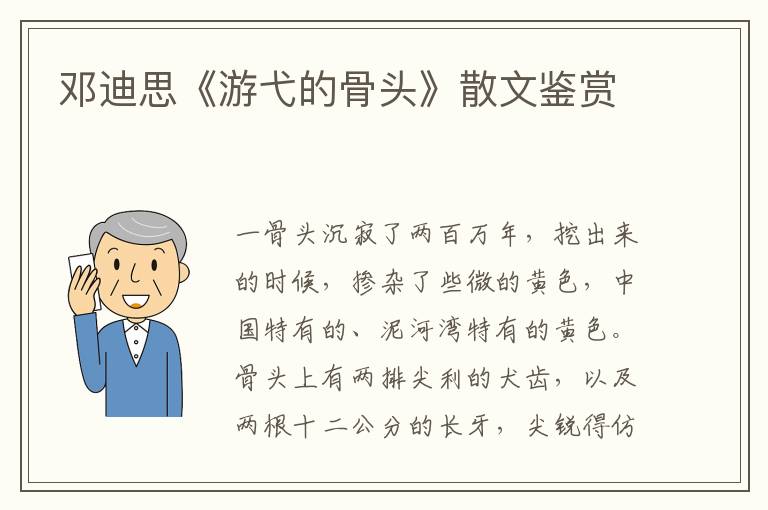
一
骨头沉寂了两百万年,挖出来的时候,掺杂了些微的黄色,中国特有的、泥河湾特有的黄色。
骨头上有两排尖利的犬齿,以及两根十二公分的长牙,尖锐得仿佛随时会戳穿身体。可以想象这个怪物悄悄靠近你,突然杀出,在你喉咙上挑开一个洞,你嗅到鼻腔中一股浓浓的腥臭的热气。恐惧?还是惊悚?所有的形容词或许都会失效。
一分钟就能结束一条生命,这个怪兽是如此迅捷。可夺命的对手并不比它强大,那些泥河湾盆地的猿人,仅仅靠打制的石头和削尖的树枝,呐喊和火把,耐心和意志,以及人多势众,击败了它。
骨头旁还有冷杉化石,这种白垩纪晚期出现的植物,在地球上繁衍6500万年之久,直到今天,还在四川的高山上、小兴安岭上,抬着它们骄傲的头。它们还在,剑齿虎已经灭亡了。
或许剑齿虎是从美洲移居过来的。冰河时代,海平面下降,它们顺着白令海峡那些露出的大陆架,或者是连成一线的岛屿,一步步地走过来。它们也历尽艰辛,可还是没逃脱被猎杀的命运。
它们四海为家,哪里有丛林,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家。
泥河湾的冷杉,和加利福尼亚的冷杉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高高的树冠上也有一些史前鸟类在鸣叫。
瓦蓝的天空也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土地,是一种黄,厚重的、中国味道的、浸入血脉的、打通经络的黄。
这黄土,最终将它们掩埋、石化,形成一块块沉默的骨头。活着的时候,它们在空间中游弋;死后,它们在时间中游弋。
一切都在游弋,冷杉的种子是会飞的。鸟儿是它们的史前客机,随着鸟粪降落,随后在这块丰饶的盆地安家,成长。冰川在游弋,海岸线也在游弋,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将游弋当作毕生的事业,尽职尽责地完成它。
二
骨头是奇怪的,像马又像牛,鼻骨上有一个断面,可能耸立过一只巨大的角;额骨上也有一个小隆起,可能是另一只角。高低搭配、错落有致是种美感,蠢笨的犀牛也有玲珑可爱的一面。
《山海经》是荒诞不经的,而荒诞的表象中总有一些真实。经上有一句话:“有兽焉,其状如马,一角有错,其名曰‘矔疏’,可以辟火”。大概这只犀牛就是那个可以辟火的矔疏了。司马迁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奇怪的动物,夏朝之前它们就灭绝了。从阳原县官村的小长梁里刨出来的骨头,让我们对古人多了一丝敬畏,一万年口口相传的历史也是历史,他们对一种消失的动物保持了长久的兴趣。
华夏古人可以记录得再详细一点,它身上有毛,这是一只披毛犀。史前一万年它在泥河湾奔跑,我们的祖先还在捕捉它。只是不知道用来烤肉,还是避火。
它的形象,从这个嘴巴游弋到那只耳朵里,代代相传,然后就成了“辟火”神兽。语言是个生命体,在游弋中生长变化,每一次传递都会增加一些信息,从食物变成怪物,从怪物变成神兽;传递者的姿态不断矮化,从平视到仰视,再从仰视到敬畏;从征服一个实物到被一个虚像征服,这就是神的文化。造神者编织神话,也是编织笼子,这个笼子关住别人,也关住自己。
辟火神在游弋,从北向南,到了苏门答腊,失去角和毛,几乎濒临灭绝。尽管它是神的近亲,但没有人崇拜它。它在适应环境上是个低能儿,需要被人类小心呵护,才能逃脱从地球上消失的命运。
大地在游弋,游弋时会唱歌,歌声就是喷发的岩浆。十万年前,大同火山群爆发,毁掉一个9000平方公里的湖泊,并震出一条峡谷,湖水东泄,那壮观的场面只有创世纪大洪水可比。之后留下一个适宜生命繁衍的盆地,一条养育万物的大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有的生命都在游弋。
一代代的神在游弋,神是集建设性和破坏性于一身的怪物。
冰川在游弋,四次大冰期,历时几亿年。十四次更新世冰期,每次历时十来万年。而温暖的间冰期,只有一两万年。生命,包括人类,不过是在间冰期苟延残喘的一群过客。
任怎么游弋,终将变成一堆骨头。骨头会说话,会说出火山灰遮天蔽日的惨痛,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一切抗争都是徒劳。明晃晃、白森森的冰川,会冻结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繁盛的文明。几度毁灭,几度兴起,人类不过是时间面前一群踉踉跄跄行走的骨头。
三
马骨没有蹄,每只足有三根趾骨。没有蹄的马跑不快,只能是猛兽的猎物。有三个脚趾、没有翅膀是个悲剧,只能靠生殖速度来弥补奔跑速度的不足。食量大,消化不良,这神奇的马贴地行走又缺乏克制,还要吃更多的草,贪图更大的草场。
劣势动物占据优质资源,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就算它进化出了蹄,变宽了门牙,退化了犬齿,也不能占得任何先机。
三趾马是原始人的食物,容易捕捉,也容易驯服,吃剩下的骨头,有几块在时间的游弋里演变成石头。它们进入人类牙齿的数量,应该比进入剑齿虎牙齿的数量要多。骨头与骨头的碰撞,是史前时代的主要交响乐,比贝多芬的《命运》更为悲壮。
如果不是人类发现马的四条腿可以替代人的两条腿,马早就灭亡了。它们应该以做人类的奴隶而荣幸,甚至自豪。一个常年驰骋在草原上的动物,以失去自由为幸福,这就是马的哲学。
马是一个天生的游弋者,身体在游弋,身份也在游弋。马伴随了人类社会整个古代史,炎黄尧舜、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英雄人物总是以马背上的征服者自居。马貌似可以获得人类的尊严,有一个属于它的名字,乌骓、赤兔,极少数马载入史册。大多数马只是工具,拉车耕地,胯下坐骑,是一种活动的商品,具有物的属性。
马是低贱的,别赞美它,它只是一个低头走路的工具。诡异的是,因为它是工具,所以大量繁衍,成为脱离自然界、踏入人类社会的幸存者。它的种类和数量一度繁盛到让自然界动物眼红的地步,在人类异化之前,马早就异化了。
人类选择了它,也会淘汰它。汽车来了,马开始退场,只有少数优良品种,存留在赛场上。淘汰的都是平民,留下的都是貴族,一匹赛马要比一辆好车贵。
从食物到运输工具,从工具到宠物,马没有犯什么错,它唯一的错误是选择了一个神,一个能将它驯化的神,它的命运完完全全捏在这个神的手心里。
马可以遥望一棵树,一棵高山上的冷杉,一个不会动的生命有它生长的自由,而这个四蹄腾尘的动物却没有自由。
它的祖先深埋在泥河湾的红壤里,被挖掘出来,陈列在博物馆中。它在动物园的笼中,咀嚼着干草,充当一个活动的标本。
它会说,上帝和它开了一个玩笑。
四
长长的弯曲的象牙,皇冠式突起的头骨,一副王者气派。这是泥河湾丛林的王,纳玛象,巨大的体型,坚韧的厚皮,似乎没有什么对手。
只是,这些骨头都是零散的,还有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它们已被吸取骨髓。骨头和石头堆在一起,被不同程度地加工,显然,这是原始人类的厨房和餐厅,那些象王,在这里被宰杀进食。
或许是某种愿望,吃了它可以力大无比;或许是稀罕它那美丽的长牙;总有一种理由,让两百万年前的人类迷恋纳玛象。
迷恋的结果是杀戮,在母象前把小象杀死,或在小象前把母象杀死,象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不是稀罕事。死亡是每天都要发生的,每一天,都会看到不同的生命死去,活着是唯一的意义。
分割纳玛象的时候,牙一定会被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然后进入仪式,对尸体的一部分祷告。生命一旦消失,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不是神,就是鬼。纳玛象运气是不错的,充当食品之后再被当作神来对待。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对着象牙说出自己的愿望,有多少个愿望,就有多少种语言。语言也许不是在劳动号子中,而是在祈禱中产生的。纳玛象以自己的悲惨命运来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延续,这也算一场贡献。它的肉游弋到人类的肠胃里,它的牙游弋到人类的供桌上。这是一场牙祭,存续了两百万年,在三星堆,还可以找到一颗牙,一颗长长的牙。
摆脱群体灭亡的方式只有游弋,其他种类的象向南方迁徙了,它们适应了更热的环境。想活下去就得改变自己,这就是进化。进化也有可能是退化,自然无情,好不容易变化出来的优点,在灾难面前,也许全是缺点。
每一次重新进入冰河期,生命就得重塑自己。变化得慢的,就会被淘汰。
纳玛象是被淘汰者,它们过于依恋泥河湾的大湖,走不出这片丛林。这个王者气质的庞然大物,其实是娇气的。它们身上有毛,可是不够厚,往南走,觉得太热,往北走,又觉得太冷。于是它们徘徊在这片温暖湿润的风水宝地,等待人类把它们全部杀光。
存活下来的,不是这种高贵的生命,而是一些低贱的、游弋的生命。
五
骨头一定要找到,骨头是如此重要。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皮韦托、步日耶、贾兰坡都在寻找,一个地层一个地层查看,但骨头躲躲藏藏。
东非的奥杜威峡谷,和泥河湾出奇的相似,既然他们找到了夏娃,为何我们不能找到盘古、伏羲、女娲?
马圈沟一百万年到两百万年的土层中有大量打制石器,和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就是没有一块头盖骨。
我们想念一幅岩画。云南沧源,两万年前的一个画家,描绘了盘古的形象:头上有光,左手持斧,右手持木,两腿直立,傲视群雄。
顺着时间追溯,也许是解构的,就像辟火神是一只披毛犀一样,也许我们的盘古,只是一个貌不惊人的猿人,拿着一把粗糙的石斧,刚刚杀死了一只转角羚羊,或者双叉四不像。开辟鸿蒙的盘古,是一个为一日三餐奔波的凡夫俗子。
神碎了一地,或许只剩下头盖骨、指骨、股骨,泛着石头的青光。在神的意义上,我们尴尬、齿冷;在人的意义上,我们感觉到一丝潮湿、温热,和微微的心动。
我们看到了自然,还有那些不加修饰的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个箭头是指向生命本质的,和自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另一个箭头是指向繁荣的,不断地隔绝自然。
人类越来越趋向于聚集,在城市,文明程度似乎可以用离自然有多远来丈量,生命的优雅、高贵、时尚可以用摆脱多少自然属性来评价。
人类在脱离自然的节奏中游弋,把自己变成神。这个神最终要离开肉体,把意识植入电脑芯片中,成为一个不依赖生物的存在。然后人类可以没有森林和草原,没有空气和海洋,可以在太空中游弋,可以在毫无生机的火星生存发展下去。
任何色彩单调的星球都可以移民,只要有能源、能量、化学元素。
在黑漆漆、泛着星光的宇宙中,在飞船上,我们或许会怀念一棵冷杉,它的枝杈还在努力触摸天空,它的细叶还在舔着阳光的味道。
我们怀念闪闪的唇光,肉体与肉体的偎依,春潮涌动时的每一个细节,还有那些两百万年前就在大地上追寻幸福的游弋的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