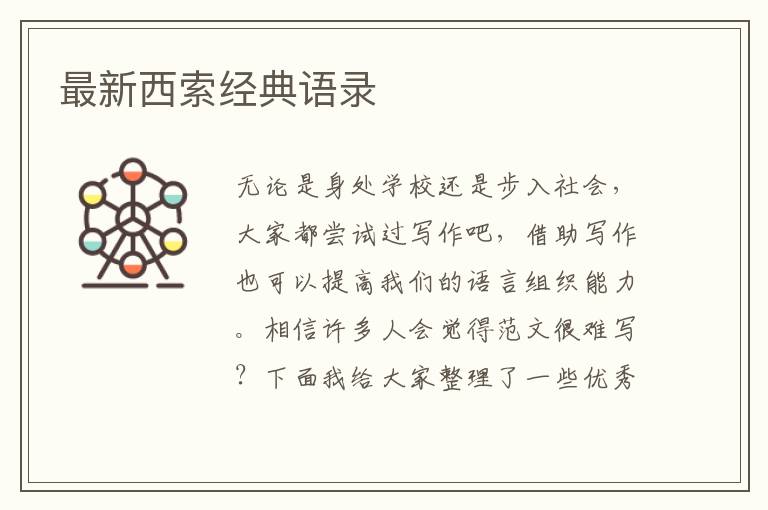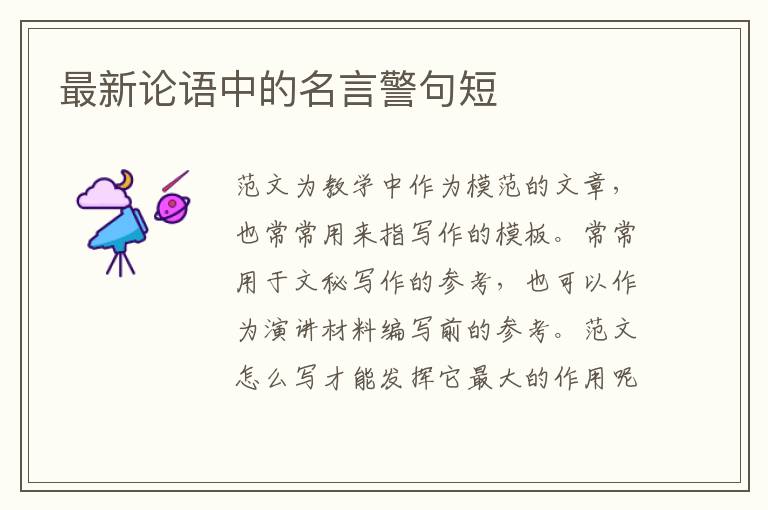与档案有关的格言集锦50句

与档案有关散文
很长时间没更新博客了,有人打电话问我,你玩儿失踪呢?!
说实话,我这个连撒谎都有些蹩脚的人怎么会玩失踪呢?!之所以不能更新博客,那得怨我妈,因为我一心不会二用,。
小时候,我妈常常教导我一心不可二用——我是个死心眼,就把这话牢牢记在脑子里了,也照着这话的意思去做了。可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同一时间段内,我只能做一件事。比如,我妈说,你去打一斤酱油,再买一包花椒面回来。我去了。可回来时准得忘一样,不是忘了打酱油,就是忘了买花椒面。当我妈发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时,习惯已经养成,想纠正已经来不及了。直到现在,我也是在同一时段内只能干一件事。
我说这事的目的,是想给两个多月不更新博客找个原由,因为在这个时段里,我正在办着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起因得从老岳父说起;这是今四月中旬的一个中午,老岳父从双榆树公园玩耍过后回来吃午饭,他说在公园里听人说国家有规定,丢失档案现在能补。
我听了之后心里一阵恶心,怒火就从胸口烧到了脑门儿。
我是一九九三年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文化馆自动离职闯荡北京的,从一九九六年受聘于《人民文学》杂志社开始,我就不断地回家乡寻找我的档案,这期间,能管得着我的文化馆馆长换了四任,文化局局长换了五任,人事局局长换了三用任;关于我的档案,从查查看,到帮助寻找,从宣告档案丢失,再到请求补办,在这十二年间,我利用工作之余往返了十一次,所有我认识的当权者,见了就说要请我喝酒,一提补办档案的`事就全退了,更有一位当权者对我说,你现在名气也有,钱也不缺,扯这事干啥,多麻烦呀!
当时也是因为工作太忙,不能长时间的坚持下去,只得一次次败退回京。
听岳父这么一说,在愤怒之余,我咨询了国家人事部、国家档案局、国家劳动部、国家社会劳动保障部,他们都说丢失档案各地都能补办,还可以参加社会保险。接着,我又咨询了岳成大律师,岳成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找徐阳律师,说她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行让她跟你去一趟。我把电话打过去,徐阳告诉我说,档案是单位给弄丢的,又不是你弄丢的,你自己回去找他们办就行,如果他们说不能办,你就到法院起诉,这是必须给办的,除了补办档案之外,如果你还有其它要求,那就得到劳动仲裁委员会——不对,你是文化馆的,属于机关事业,应该到当地的人事仲裁委员会。这事百分之百能给你解决。
听过了,我大喜过旺,喝了点小酒,准备出发。在出发之前,又跟综合频道、法治频道相关的几个哥们儿打了个招呼,让他们准备一下,如果家乡领导不作为,我就叫他们去做一期节目,给他们爆爆光,跟他们鱼死网破。
出发前,老婆说,到那别废话,直接就起诉。我说,还得先礼后兵好,现在文化局跟体委合并了,叫文体局,我哥们儿张书君在那当局长,总不能不打个招呼吧!
于是,我带上马原送我的《悬疑地带》、阿成送我的《欧阳江水绿》、孙春平送我的《江心无岛》、聂鑫森送我的《诱惑》、柳建伟送我的《突出重围》、邱华栋送我的《摇滚北京》和方青卓送我的《情坠洛杉矶》等几本书,带上笔记本电脑上路了。我想,回到家乡,跟现任局长打一招呼,然后上法院一起诉,文体局就得乖乖地去给我补办档案,在等待期间,我把这些书都读完,然后再写点东西,等事情全办完了,带上补好的档案、带上养老保险的手续回北京,从此咱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了。
没想到,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顺利,在补办档案过程中,富拉尔基这座家乡小城里发生太多的故事,从现在开始,我会一心一意的把这些故事一段一段地写出来,让各位品味品味小城里的滋味。
档案丢了散文
办事难, 事难办, 到处求人陪笑脸;世态变, 人情淡, 遇事求人的花钱
——题记
天天想、夜夜盼,终于盼到这一天,从2008年3月份单位宣布改制破产到现在,将近4年的时间,期间,大小会开的无数,职工上访的次数也不计其数。说真的,要不是讨口饭吃,象政府机关这样的高门楼,我们这些贫民百姓,是不敢大摇大摆、厚颜无耻的进出自由。
记得2000年腊月二十四那天上午,经协商,我们三个《酒厂、大修厂、印刷厂》破产单位几十个人聚集在县长的办公室,七嘴八舌的议论着,都希望有关部门抓紧时间,把我们这二百多名职工的失业手续尽快办妥。其实,大家的要求不高,只要把我们的养老金交到当年年底,按国家政策,下岗职工该得的钱发给我们就行,大家都想早一天和单位脱离关系。
常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的日子最难过,没钱的县长更做难,这几年,一任推一任,谁也不想来管这难缠懒手的事情。记得当时县长说:“没事,请大家放心,无论如何,非达到你满意不成,到时候,每人给你们发几万元的钱,让你们个个都笑着回家过舒心的日子”。
也许是领导心情不好吧!他指着一位职工的脸恶恨恨的说:“我就知道,每次上访就少不了你!”那人也恼火,扯着嗓子说:“你把问题解决了,你看我还会来找你不。”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吓得不敢吭声。
现在,总算有结果了,按国家政策,所有破产单位职工的安置手续,必须在年底前清算结束,事情到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本月15号那天,单位通知说:“每人准备八张一寸照片,八张身份证复印件,带上户口本去填表,交养老保险金和失业金。”
当我手持各种证件去填表时,我傻眼了,一百多号人都有档案,就我的档案丢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辛辛苦苦上了一辈子的班,现在是个黑人,没档案,领不了失业金暂且不说,更让人愁心的是,过两年退不成休咋办,我慌了手脚,四处打电话追原因。
我87年10月到果酒厂上班,当时,待业青年太多,想有个正式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人事局组织岗前培训学习,结业后发证,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那一年是人事局招收第一批全民合同制工人,果酒厂,植物油厂、化肥厂等几个厂矿,安置职工200多名,我就是其中一员。
起初,酒厂系商业局下手单位,所有的档案由局档案室保管。此后,几经改革,酒厂统一划拨给经委领导,最后又原班人马转给黄金局。
当年,从商业局往经委转档案时,就听领导说:“你和夏宝娟两人的档案死活找不到”,我问咋办?他们说:“没事,统一转过来”,我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总想没事,再说一同进厂的26名职工,有权有势的人,都调到好单位,我没关系,就在原单位熬到今天,应该没事。
鬼知道,档案这么重要,档案是退休审核时绝对重要证据,没有档案,你就有一百张嘴给你说话,理由再充足,还是办不成退休手续。
从15号(星期三)下午,我开始跑到档案局、人事局、商业局等单位。先到档案局,人家告诉我,管档案的人有事在家休息,星期五才上班,我认识她,打电话求人家帮忙,星期五八点钟,又去找她,她说:“有难度,不过尽量给你查查,还说,别看这张纸,在有些人手里是废纸一张,有的人就是花上十万八万也难找到”。我想,同时招收一大批工人,应该有文件,信心十足的等待结果,等到的结果是:“实在是找不到,是不是时间说错了”。
我又跑到人事局办公室,在人事局,我算真正的见识到,大官的威风,说话气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模样,一个有四十多岁、中等个子、白脸、大眼的'干部,说话死难听,吹胡子瞪眼说:“你的档案丢了与人事局无关,谁弄丢你去找谁,就这,我已解释清楚,你也别再问,我一句话也不多和你说。”我说:“我不是来找事,想问问这种情况该咋办?”嗨!真是活见鬼了,撞见这样的愣头青,事情没问出个原因,还塞了一肚子的气,我厚着脸,转身走的时候,甩出一句话:“要不是档案丢了,我才不会踏你们人事局的高门楼”。
这几天,我不停地跑来跑去,档案局、商业局、黄金局、社保所、教育局等单位,见到好多人,不管是能不能办事,服务行业的人说话都好听,没有象人事局那位大干部那样说话气粗。
礼拜天两天,我跑到单位查文件,可是单位的文件也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也查不出有价值的东西,20号那天晚上,我整整一夜没睡好,满脑子想的全是,万一查不到原始文件咋办,越想头越痛,没法子,只好吃个安定片,迷迷糊糊的熬到天亮。
还好,谢天谢地,也许是老天可怜我吧!又托关系、找亲戚、提礼品、说好话。星期一下午,总算找到当年招工的花名册和原始红头文件,清楚地看到我名字的瞬间,我高兴地几乎跳起来,一个劲的说:“谢谢、谢谢、吃啥、喝啥、我请客!”都是熟人,他们都替我高兴。
虽说我费尽心血找证据、补档案,期间,也遭到他人的冷言冷语令我恼恨一辈子的人和事,但我不后悔,值得,档案啊档案,我的命根子,我后半辈子的生活支柱,不知道,找不到你,我会气的咋样?
唉! 说一千道一万,补好档案是我最最开心、高兴的一件事。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替我高兴吧!
土地档案散文
我们家的猪牛猫狗什么的都有名字。那条毛色黑亮的狗,我们叫它黑狗,那只羽毛黄红间杂的公鸡,我们叫它花鸡。我们家的田地也都有名字。我们家种了三亩土地,算起来,大大小小的田地共有十二片。这么多田地,当然得一一给它们取上名字,不然容易乱套。比如,要上地里干活去,却不说是哪块地,一家五六个人,有的扛着锄上山,有的架着犁下河,那成什么样子?而一说“沙地”或“弯弯田”,都就明白了方位,都朝那里走,事情就简单多了。
【第1句】:沙地
沙地是我们屋后樟树边那块地的名字。这地沙性重,雨水一浸泡,土壤就要板结。土壤一板结,禾苗就长不好。一年之中,下雨的日子总是很多,因此,为料理好这块地,让它长出好庄稼,我们费了不少的劲。我们在这地里栽种的主要是红薯、小麦或油菜。
这地离我们家最近,一有空闲,譬如饭前或饭后的那点闲余时间,我们总要到这地里看看,或者侍弄点什么。春天,小麦或油菜长起来了,看禾苗是不是齐整,哪块地方的苗子稀了黄了,得给那儿补施一点肥水,如果禾苗上生了虫,得喷些药。夏日,看地里是否有旱象,是否长了杂草,有,当然赶紧设法解决。因为离得近,我们对沙地的照看要比其它田地周到,这地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也能随时知道。
现在是五月中旬,沙地成了一块空地,正闲着。十天前,这地里还是一地油菜。那时,沙地正努力地把快要成熟的油菜养得籽粒更饱满些。土地养育庄稼,就像母鸡孵蛋一样不声不响,菜籽角不知不觉间一天天肥硕粗壮起来,压得菜秆互相扶持着也还是撑不住弯腰欲倒的样子。那天,我们见菜籽熟得要在阳光里炸开了,就割了回来堆在院坝里。
油菜收割之后,沙地就闲了起来。
但这时,沙地四周其它田地正在忙着长庄稼。左边是陈海家的一地麦子,麦子一天一天黄起来,赶路似地往收割季节走。右边是陈大安家的莴笋地,莴笋日渐长高,叶子一日赶一日地阔大起来。上边那块地是陈小强家种的油菜,还没成熟,得等上三五天才能收割。下边那块地又是陈海家的麦子……
闲下来的沙地,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感觉是空荡荡的。早上,村路边的野草上都挂着露水,沙地四周几块地里的麦苗上、莴笋叶上也湿漉漉的,我们家的沙地里什么也没有,空空地袒露着一地泥,露水直接落在泥土上,泥土就湿润了一层。
两天前,我们从沙地边路过,见地里零星地生出了一些嫰嫰的野菜。父亲说:“土地是闲不住的,没有禾苗生长的时候,它就要生长野菜、杂草。一年四季,它总是没有歇息的时候,不像我们人。”
父亲说得对,我们人劳累一阵就想歇下来喘口气,什么也不干,让时间白白流走那么一段。土地却是从来不歇息的,它一直都在忙着生长什么,年复一年都这样。
野菜长起来了,这是沙地在提醒我们不要让它闲得太久,在催促我们要及时播下另一个季节的种子。
“加紧收麦子吧,收了麦子,快来这里栽红薯。”我们从沙地边走过时,父亲这样说。
过两天,也许就是明天或者后天吧,我们要来翻耕这块沙地,然后栽红薯。
【第2句】:麦田
麦田原来叫方田。包产到户那年,它给分到我们家后,我们就改了名叫麦田。这田也怪,专能长麦子,村里那么多田地,一年要种多少麦子啊,可就数这块田里的麦子长得好,收成好。别的庄稼,比如油菜、大豆什么的就不成,这些东西在这田里总是长不好,肥施少了,苗子又矮又瘦,肥施得稍稍多了点,苗子就猛劲儿往上窜,又高又壮,但到秋天收获的时候,收成却比同样面积的其它土地少得多,还是欠收。既然麦子长得好,我们就叫它麦田了。
麦田位于村子东边的一条大路边。那条路从邻近的村子伸过来,然后蜿蜒着又伸到另一个村去。每年二月到五月,从麦苗长起来到收麦这一段时间,一拨又一拨的过路人经过这里时,总要惊惊诧诧地说一句:“哈呀,多好的一地麦子!”
麦田是在分给我们家以后才长好麦子的。父亲说,大集体生产那会儿,一个队里二十多号人都来这田里种麦子,可地里老长野草,麦子差不多每年都长得像一地狗尾巴草,麦秆又细又矮,风一吹,轻飘飘的麦穗乱晃荡。麦田在那个年代出不了麦子,就像一个人耽误了好多年的青春,什么事也没干。
后来土地下户了,父亲对我们说:土地生来是长东西的,你在地里种瓜,它就长瓜,种麦它就长麦,种得好,它就长得好,什么都不种,它就什么也不长。一句话,土地是没有过错的,有错的话,那是人的错。我们明白父亲的.意思——麦田分给我们了,我们得好好侍弄。
自从我们家种了这块田,它就再没长过野草什么的,一年一年春长麦子,秋收红薯。当然,村里所有的土地这以后都没长过野草了,长的都是好好的庄稼。
记得麦田分给我家的第三年,是四月初吧,有天傍晚,父亲从地里回来,路过麦田时,他想看看麦子的长势,绕着田埂走了一圈。麦子长势当然好得很,父亲很满意。但父亲发现一件奇怪的事,麦田中央有一片麦苗摇晃得厉害,像有一阵风专门对着那儿吹。可是那天傍晚根本没有风,村里风平浪静的。父亲决定看看究竟,侧着身子顺着地沟进入麦田,一看,原来是一对小男女藏在麦田里亲热。他们不仅把我们的麦子弄得摇晃不已,还压倒了好大一片。那对小男女一个是邻村的,一个是我们村的。我们村的那个一见父亲来了,吓得拔腿就跑,像兔子那样三窜两窜就不见了,扔下邻村那女子不管。父亲有些生气,在后边追着喊:赔我的麦子,狗东西。“那是多好的麦子啊,他们给压倒了好大一片。”父亲回来跟我们说的时候,还是忿忿的样子。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诗经?丘中有麦》的时候,才知道麦田自古就是男女相恋的去处。“丘中有麦,彼留之国。彼留之国,将其来食。”(我在麦田里长久地等着你,远方的心上人。远方的心上人呀,我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食物。)不知这位多情的古代女子是否等到了她的心上人,不知这对相恋的男女是否也压倒了田里的麦子。
【第3句】:新地
新地是我们在桑园坝那片荒野里新开的一块地。
村子南边的桑园坝实际上没有一棵桑树,好多年来,那一大片土地上只有野草在生长。连片的野草春天长起来,秋天枯萎下去,自生自灭。那似乎是一片没有用处的闲地,年复一年地荒芜着。
有一年,父亲忽然对这片荒野动了心思,带我们来这里垦出一片地,然后种上麦子。我们一带头,村里许多人家都来这里开荒种地了。现在的桑园坝不再是荒野,一大片田地里种满了庄稼。
新地刚种庄稼那两年,我们没指望有什么收成。刚开垦过来的处女地,泥土是生的,地性野,能长好什么呢?种了几十年地,我们知道土地跟其它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也有它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过程,要让一块生地长出庄稼,得首先把这片土地养熟,就像把一个瘦弱的女子养得白白胖胖才能育出健康的孩子一样。我们不断在田地里忙活,表面看来是在侍弄庄稼,实际上是在养育土地——把生土养熟,把瘠地养肥。新垦的土地长不出庄稼,不是土地不好,而是我们还没有把它养好养肥。
我们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把这片瘠地养肥。我们不断在地里翻耕,捣碎粘结的土壤,捡出瓦砾,除去草根,施肥,浇水……土地跟我们养的牛羊一样,驯顺而有灵性,时间一长,它明白了我们的心思,渐渐脱去野性,不长野草了,一心一意给我们长起庄稼来。头两年,它还像个刚理事的新手,慌手忙脚的,庄稼长得不咋样,但第三年,它什么都熟惯了,把我们种下的麦子当成自己的麦子那样养育了,春天,满地的麦苗齐齐整整、嫩嫩绿绿地茂盛,是全村最好的一地麦。到夏天,新地给我们产下九百多斤颗粒饱满的麦子,而当初播下的麦种不过百十来斤。
我们终于把这一片野地养肥养熟了。新地成了我们家的一部分。
【第4句】:屋边地
我们房屋右边有一块地,不大,约一分面积,通常只种些家常小菜,比如四季豆、茄子、丝瓜、辣椒、蒜苗。这些蔬菜都是随时用得上的,种在家门口自有好处,比如,米已经下锅还没有摘菜,菜下锅了还没有蒜苗,那好,马上去地里摘几把回来,——叶子上还有露水在滴呢,鲜炒现吃,方便得很。
但是,距房屋太近了也不好:鸡鸭老在地里糟蹋。种子刚下地,它们就溜进去东刨西抓,弄得地里到处是坑;菜苗长起来,叶子还很小,就给它们一嘴一嘴地蚕食,只剩小小的茎在地上秃着。这是很令人头疼的事。
鸡鸭这东西是不讲道理的,我们只有哄赶。大声吆喝,或者拿土块打。即使它们不在地里,只在地边转悠,我们也不放心,非要赶到远远的地方不可。我记得,每到种子下地,我们就开始吼鸡吼鸭了,天天吼,吼得它们看见人的影子就炸着翅膀跑。
但哄赶也不是良方,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不能总在地边守着。所以后来就采用另外的办法:用栅栏把整块地围住。栅栏是用树枝和竹片密密地编织而成,有人多高,鸡鸭进不去,别的什么东西也不容易进去。这样,这地就安全了,不再担心鸡鸭或牛羊的打扰,一心一意给我们长菜。到春末夏初,地里绿汪汪一大片,肥胖的叶子把地遮得严严实实,而丝瓜的藤蔓,一条一条牵到栅栏上,晃眼一看,仿佛是干枯的树枝又复活了,长了那么多鲜活的嫩叶。再过些日子,张着嘴的丝瓜花就喇叭一样绕着菜地呜哇呜哇吹起来。
菜地里那样热闹,鸡鸭们是很羡慕的,在栅栏外面伸着长长的脖子张望,它们走过来走过去,心里七上八下不能安静。那样子叫人好笑,又有些可怜。
到秋天,这些家常小菜败势之后,我们就在这地里栽种灰菜。灰菜的学名叫磨芋,这是一种懒庄稼,鸡鸭也不感兴趣,我们就让它自己长,忙别的活去。这时的栅栏还在地边围着,不过没什么实际用处了,日晒雨淋,慢慢就朽坏了。
第二年春天,我们又在这地里种小菜,同时把坏了的栅栏拆除,重做了新的栅栏。
年年都这样。一块地,每年修一圈结实的栅栏把它围着,我们从不觉得麻烦。
【第5句】:旱地
这是我们屋后山包上的一块地,呈葫芦状。因为地势较高,又没有水源,常年干旱,所以叫它旱地。
这地我们秋天种小麦,夏天种稻子。收成当然不好,旱得凶的那一年,禾苗枯得像一地茅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所以每遇天旱时,我们就为这地担心。
为了解决干旱的问题,有一年,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地边挖一个坑,用来蓄水。水坑的位置要比地高,雨天把山水引进去,蓄满,到地里旱起来的时候,就把水放进地里灌溉。水用完了就再蓄。
但是日晒风吹的,水蒸发得很快,一坑水蓄在那儿,并没有灌多少到地里,不久就只剩半坑了。这跟把粮食蓄在仓里,把念头蓄在心里一样,结果总是这样的:蓄着蓄着就有好些不见了。
后来我们把坑扩大,装下的水比原来多了一倍。这样一般的旱情就能抗过去了。再过两年,我们又把它扩大,像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了,装下的水更多,这地的灌溉就再不是问题了。
这时候我们担心的是牛去池塘里滚澡。天热的时候,不论是黄牛还是水牛,见到水坑就要去滚几滚,如果是大的堰塘倒没有什么,我们的水池小,牛到里面一滚,水就四处漫溢,几条牛一齐滚,那就会水漫山坡,池塘里就剩不下多少了。为这事,我们还跟一些人说了红脸话,比如三叔,他的牛一次又一次跑到池塘里滚澡,每次都浪出很多水,水白白地流走了,叫人心疼。有一回母亲就把三叔喊到池塘边,指着四处漫流的水忿忿地说:“你看你的牛,把我们这一塘水整得像个啥,这些水是救命的,救谷子的命,也救人的命……天旱了我们拿啥灌苗?你去河里给我担行不行?”三叔红着脸无话可说,当即把他的牛狠狠打了一顿。
打一顿又怎样呢,牛是那个德性,照样要滚澡的,这家的牛不去那家的牛去。没办法,还得靠我们自己好好盯着。
【第6句】:水毁田
桑园子有一个水田,紧傍着山坡,我们叫它傍山田。这田夏天栽稻子,秋天就耕过来种小麦。两季的收成都不错。
有一点不好,就是种稻子的时候,只要下大雨,山上的洪水一下来,这田盛不住,田坎的某一段就轰地一声崩溃了,那个声音和阵势,很吓人。
田坎一垮,水都哗哗地流个精光,稻子现时要受旱,秋天要减产,所以每次山洪过后,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田坎修好。修田坎不是轻松活,需得先用石头在崩溃的外围码一道矮墙,再拿泥土把缺口筑起来。如果崩溃的只是一小段,也费不了多少事,小半天就能弄好,如果口子又大又长,那就费工夫了,两个人干一整天也不一定能修好。
偶尔一次倒也没啥,问题是,隔两年就要给冲垮一回。上次是这里垮,下次是那里塌。
我们想过不少办法。比如把山上的堰渠理好,将山水引开,使其不往田里流。但洪水大了,堰渠也会给冲坏,山水还是下来了。比如把田坎加厚筑高,但要是雨下得太大,大到山体都滑坡了,这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该垮还是要垮。
没办法,只好隔两年修一次田坎。
【第7句】:漏水田
这田在风包岭。这田有个毛病,隔那么几年,突然就关不住水。特别是五六月份的时候,稻谷长得正好,田里也蓄了满荡荡的水,可是才过一月半月,水就悄无声息地少了一大截。说蒸发吧,哪有蒸发得这样快的?说流走了吧,又不见一丝痕迹。找不出原因。
找不出原因,父亲就猜测:这田的某个地方有暗洞,水从暗洞里流走了。暗洞可能是黄蟮钻的,也可能是地鼠钻的。但那洞到底在哪里?找不到。
找不到,就拿锄头把田边、田埂密密实实地筑过一遍,希望这样能够碰巧把漏洞砸实。但总是白费工夫,水还是不知不觉少下去。
正是稻秧拔节的时候,眼看着田里的水一天天少下去,又无技可施,心里干着急。
如果这个时候下雨了,就把快要干涸的稻田蓄满水,满得都要溢出来的样子,这样维持到稻谷成熟,还无大碍。如果天旱,老不下雨,那就只好看着稻田干下去,看着禾苗枯萎,最后看着粮食大大减产。真叫人心痛。
到下一年耕田栽秧的时候,父亲就在这块田里花很多工夫,一犁耕过来,一犁耕过去,仔细得很,生怕哪里少耕了一犁。所费时间和精力比其它田地要多得多,就说拉犁的牛吧,耕完这田就累得趴在地上起不来,得把草背到地里,堆在它嘴边,它卧在那儿有气无力地细嚼慢咽。
父亲的意思是,耕得细致一点,好好把泥拌一拌,拌熟了,慢慢的,熟泥也许就能把那暗洞给堵上。
也许真是这样,他这么一弄,当年就没再漏水。第二年没事,第三年也没事。你以为可以放心了,但偏偏是这个时候,第四年,突然又漏了。于是又费很多工夫去耕田。
这田,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关《流光》的散文
再后来,他离开以前的工作单位。慢慢地,越来越少喝酒,越来越少应酬。他依旧喜欢动画片,犹爱《蜡笔小新》;他依旧喜欢讲冷笑话,诸如“妇女节”其实是“父女节”。
是谁说的,“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我曾暗暗揶揄这句话,我的眼光才不会这么差。现在我想,这也许是真的。
安意如说:“关于光阴的流转,是蒋捷说的最美: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我曾深以为然,我和父亲,都成熟了。
但我发现,我又错了。
四十多岁的男人过着二十几岁年轻人的生活,修补着曾破碎过的好物。听起来不错。但是我忘了,父亲不是超人。毕竟四十多岁的人啊,毕竟从前很少受过苦啊,毕竟他是从小被宠着的老小啊。
那天晚上下晚自习,妈妈来接我。
“爸爸呢?”
妈妈眼中有一丝无奈和不忍:“他在家睡觉。”
八点四十而已。
“他怎么不来接我!”
“他今天太累了……”
一时之间,我竟丧失了言语功能。
他,太累了。
我却,一点没有发觉。
我想笑。他伪装得太好:他依旧给我编冷笑话;依旧跟我打嘴仗说我腿粗;依旧让我打他明显变小的肚子。可是我忽视了,七十岁的爷爷依旧满头乌发,爸爸鬓角却多了隐约的银丝;他曾号称有“航空眼”,如今看报却不得不戴上老花镜。
岁月真是把杀猪刀。我曾以为我和父亲都变成熟了,现在才发现,他不是成熟,是变老。
回到家里,到主卧,看见他趴在床上,背朝天花板,双臂间抱着枕头——真是幼稚的睡相。却情不自禁走到床前,替他盖好被踢掉的'被子,然后毫不犹豫地离开,跑回自己的房间,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先是啜泣,最后泣不成声。
世间好物不坚牢啊。我刚要和你勾肩搭背,你却已经变老。
“流光容易把人抛。”这分明是最残忍的诗句。
如果我可以贿赂一下流光,我倒希望流光把你抛到流光之外,岁月才你身上静止:四十岁的年龄,二十岁的张扬,六十岁的享受。
你说,好不好?